 |
《香港凤凰周刊》 记者/漆菲
从1995年开始的近三十起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诉讼案,均未能获得公正裁决,如今仍在诉讼中的仅有2件,前景皆不明朗。
当《凤凰周刊》记者在北京阜成门附近的某座写字楼内见到童增时,他正在几个办公室之间来回穿梭,讨论着好几件涉日案子。会议室内,其助手们已经准备了几大叠剪报、信件和影像资料。他倚在椅子上开始介绍,神态有些疲惫,加上支气管炎,交谈间咳嗽不止。
作为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会长,从早年的劳工、慰安妇、细菌战受害者索赔问题,到后来名声远扬的民间保钓运动,再到赴日与右翼分子激辩,以及现在的对日文物追讨——几乎所有大陆的民间涉日案,都与童增脱不了干系。2015年3月,他还作为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第一人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
20多年来,中国民间对日诉讼案不断涌现,又不断遭遇挫折。中国劳工对日索赔、细菌战、七三一人体试验、慰安妇、大轰炸等诉讼一次次将无数凄惨的故事推到台前,渐渐又淡出视线。从1995年开始的近三十起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诉讼案,均未能获得公正裁决,如今仍在诉讼中的仅有2件,前景均不明朗。
随着日本三菱综合材料公司与部分中国劳工受害者达成大规模和解,似乎形成一个参照,让民间对日索赔滑向另一个轨道。
受害者突然“涌了出来”
6月1日,当三菱材料的和解协议签署之后,幸存劳工代表闫玉成向童增赠送了“恩重如山”墨宝。当众多受害劳工以及劳工遗属向他赠送“民族英雄”的锦旗时,童增坚辞不受。
如今的阶段性“成果”,是他在26年前不曾想过的。1990年,当时还在北京化工管理干部学院任教的童增在《报刊文摘》上偶然看到一则关于《东欧各国重提战争赔偿》的豆腐块儿新闻,法学背景出身的他开始搜集资料,并于1991年写成《中国要求日本“受害赔偿”刻不容缓》的万字长文(下称“万言书”)。
当时童增找了几家报社,但在倡导中日友好的大背景下,对日索赔算是十分敏感的话题,报社经过研究选择不发表。
1992年3月,第七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上,贵州团王录生和安徽团王工等共计70名代表以童增的“万言书”为基础,分别提出《关于向日本国索取民间受害赔偿》的议案。这则消息引起海内外巨大反响。
同年4月,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在访日前答记者问时称:“中国放弃国家要求日本给予战争损失赔偿,但是,对民间要求赔偿的动向不加限制。”
童增随后致信日本国会,要求日本天皇在当年10月访华时,就日本侵华战争向中国人民谢罪赔偿。由此,民间对日索赔的序幕被拉开——包括三菱受害劳工在内的中国二战受害者纷纷写信给他(让其转交给日本驻华使馆),更多的人甚至来京登门拜访。
第一封来自三菱被掳劳工的信件,撰写时间为1992年10月,来自于山东省高密县蔡站乡杨家庄。写信人叫杨范荣,他的父亲杨发仁于1944年10月被抓到日本秋田县路中花轮火车站,去三菱铜矿当劳工,“吃的是橡子面,出的是牛马力”,后因塌方致死。因而其要求日本政府和企业主向遗属谢罪,并进行一定的经济补偿。
类似的信件在接下来的日子堆满童增的办公室,“从1972年邦交正常化开始,国家一直讲对日友好,可能这部分人的诉求被抑制了,直到90年代初他们看到了我的文章和提案,突然觉得有一个渠道可以宣泄了,(受害者)一下子就涌了出来。”
不过,在一段时间后,官方在此话题上开始降温。虽然一开始有部分官方媒体曾转载童增的文章,但在提案被送上人大后,关于童增的报道却少了下来。记者注意到,童增收集的大部分剪报均来自香港媒体和海外媒体(主要为日媒),大陆媒体上几乎不再出现。
 |
| 2003年1月,二战时被强掳至日本京都大江山矿山的中国劳工起诉日本企业被京都地方法院驳回后,受害者家属以及中日法律人士走上街头表达抗议。 |
在日诉讼走到尽头
1994年,一个名为“中国司法制度调查团”的日本律师团来京访问,目的是恢复因文革而中断的日中司法交流。作为日本民主法律家协会事务局长的小野寺利孝律师也是其中一员。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了解到童增所做的事后,小野寺与童增相见。两个月后,小野寺成为中国二战受害者起诉日本政府及加害企业的日本律师代表。由于按照日本法律,只有本国律师才可代理他国受害者参与诉讼,小野寺的参与真正让中国二战受害者对日诉讼成为可能。
为了解更多事实,小野寺和他的日本律师朋友组成“受害事实调查团”,见了许多幸存于世的日本侵华战争受害者,如山东的被掳劳工刘连仁、慰安妇、平顶山惨案的幸存者、日军“三光”政策的幸存者、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以及日本七三一部队在中国所犯下的违反人权的重要暴行,并深受震撼。其中最多的,则是受到日本加害企业奴役的被掳劳工幸存者,其中也包括被掳到三菱材料的中国受害劳工。
“小野寺那会儿才五十多岁,他跟童会长说,这个官司我可以打十年,结果没想到打到70岁了,黑发变白发了,还没赢。”童增的助理孟惠忠女士向《凤凰周刊》感慨道。孟女士于2007年加入童增的公司,目前是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的秘书长。
小野寺的加入,带动了一大批日本律师乃至志愿者的加入。当时参与其中的日本律师有将近300名,全部是公益性质,十余万日本民众也签名表示支持。“20多年来,为了打官司,小野寺卖车卖房,最困难时连到中国的路费都掏不起了。”孟女士说。
然而,从1995-2007年,日本律师团帮助中国二战受害者打了三十多场官司,均以败诉告终。这当中,起诉三菱公司的案子共有5个,分别在日本札幌、东京、福冈、宫崎、长崎等地方法院起诉。2003年,童增还曾亲赴日本札幌法院,为中国被掳劳工出庭作证。不过,日本法庭始终以“《中日联合声明》中方放弃了中国公民的个人索赔权”为由,驳回中国受害者原告的合理诉求。
2007年,日本东京最高法院对日本侵华战争中部分中国受害者提起的两起诉讼——“西松建设强制劳工案”和“山西省慰安妇案”作出终审判决。虽然法院认定日本企业的加害事实,但仍判决中国劳工败诉,理由仍是1972年的《日中共同声明》。最高法院的判决意味着,此类案件以后很难再获得胜诉。
不过,败诉不意味着路被堵死。日本最高法院在驳回中国劳工一切诉求的判决书附言内,提出“希望曾经奴役过中国劳工的日方企业作出救济”。就是这句附言,给受害劳工们留了一扇门。
 |
| 2016年6月1日,幸存劳工代表闫玉成、赵宗仁(劳工联谊会第一副会长)、张义德将闫玉成亲笔书写的"恩重如山"墨宝赠送给童增。 |
国内起诉依旧艰难
在日本屡告屡败的情况下,中日双方的律师们也开始琢磨:能否将官司搬到中国来打。从法律层面看,中国法院对相关案件有属地裁定的权力,但一直以来还未能对此类案件作出任何司法解释。
实际上,早在本世纪初,就有慰安妇和劳工代表希望能在国内法院立案,但国内法院态度基本是拒收,即便收下来也不作任何回复。一位熟稔当中过程的中方律师告诉《凤凰周刊》,一般来说,法院收受材料要请示上级,收到材料如何判还要请示上级。“但当时无论是外交部、妇联还是全国总工会,没有一个机构明确出来说应当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它们)既不提支持,又没有人出来协调解决问题”。
童增亦承认,“国内起诉作为新的课题,最难的在于以前没做过,需要尝试,所以时间会放慢。我们希望中国司法机构可以多探讨这类话题。”
2004年11月23日,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夏淑琴诉日本右翼学者松村俊夫等侵害名誉权案,在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开庭。2006年8月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其胜诉。这被视作国内诉讼的破冰之举,有人说,这有利于把日本侵华战争的遗留问题纳入中国的司法框架内加以解决。
截至目前,至少有10起索赔案在中国国内起诉,但成果寥寥,唯一的胜利是“中威船案”的胜诉。
上世纪30年代,“中国船王”陈顺通将自家两艘轮船租给一家称为大同株式会社的日本公司,但在租期已到后被日本政府掠走,两艘船在侵华战争中沉没。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陈家三代人相继在东京、上海提起诉讼。
2014年4月19日,上海海事法院执行“中威船案”的民事判决,扣留了作为大同株式会社继承者的日本三井株式会社的一艘货轮,迫使对方执行法院判决进行赔款。4天后,这家日本公司宣布履行上海海事法院的判决,支付40亿日元的赔偿金。这场官司在东京、上海两地法院打了70年,自2007年上海作出一审判决后又反复多次,最后以中国船王陈顺通的后代获赔告终。这也成为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第一个成功案例。
目前仍在持续的民间对日诉讼还剩下2件,不过前景皆不明朗。
一件是重庆大轰炸的诉讼二审。这起针对日军侵华时期对重庆地区无差别轰炸的诉讼,在2015年2月的第一审阶段宣告败诉。近十年的一审期间,日方律师一濑向法庭递交的证据多达上千份,由日方学者和中方学者分别撰写的大轰炸鉴定报告有上百万字。
然而,这是一件不被看好的诉讼。毕竟2007年日本最高法院判决之后,新的诉讼能够胜诉的可能性就很小了。再加上诉讼对象是日本政府,更让其成为不可能的任务。此案的二审将于今年7月在东京高等裁判所开庭审理。
另一件便是被掳劳工问题。2009年,中国二战劳工法律援助团正式向日本加害企业递交律师函并提出要求:承认侵害事实,派出代表就侵害中国二战劳工人权一事,与中国二战劳工联谊会和中国二战劳工法律援助代表进行认罪和赔偿协商。受害者代理人在北京、河北、河南、山东等地法院对三菱材料公司提起诉讼。2014年在北京、河北、山东三地先后立案,但开庭还遥遥无期。种种窘况下,更多的人将注意力投向了另一条务实的渠道——和解。
以和解走向终点
2016年5月14日,蒙蒙细雨中,中国被掳往日本劳工联谊会两位工作人员与现年86岁的副会长—河北农民赵宗仁讨论着三菱的和解方案。1小时后,碗大的烟灰缸里摁满了烟蒂。最后,赵宗仁拿出自己的私人图章,在文件最后重重地盖上。
1944年被骗上驶往日本的船时,赵宗仁才14岁。在13个月的劳工生涯中,赵宗仁吃尽了苦头。1993年年初,63岁的赵宗仁从《文摘周报》上读到童增关于劳工有权利向日方索赔的文章,从此开始与童增合作,尽力寻找二战幸存劳工。
一开始,赵宗仁总被别人误以为是骗钱的,儿子赵士龙说起便嘿嘿直乐,“大家那时候哪里听说过可以找日本赔钱,我爸一上来就说,我们要找日本人给咱们道歉,赔偿咱们劳工,哪里像真话?”赵宗仁倒是没气恼,他拉着大家回忆都有谁去过日本,附近的这个村的叫什么,误解他的人渐渐打消了疑虑。
最初,他骑着自行车;后来,为了跑得更快更远,买了摩托;接着又买了个电动三轮车,继续跑;现在,赵宗仁有时候干脆就坐儿子赵士龙的轿车,由儿子载着跑。赵宗仁坐骑的轮子越来越多,跑的地方也越来越多。
“远的地方到河北、天津、山东,别人没有像我似的这么折腾,只要能找到劳工和劳工遗属的地址,没有不到的地方。”
赵宗仁把劳工的姓名、年龄、地址挨个写在笔记本上,红色的笔迹是第一遍,蓝色、黑色的笔迹用作补充,就这样,他手上的劳工名单笔记本越填越满,色彩斑驳。
从1999年开始,赵宗仁先后10次赴日本,其中9次关乎诉讼,以受害者、证人的身份出庭。
2004年,在日本北海道札幌地方法院宣布败诉后,作为原告的赵宗仁参加了央视《新闻会客厅》节目的录制,主持人白岩松问他如果之后还是败诉怎么办,赵宗仁背挺得笔直,“败诉还有机会再打,有儿子,有孙子,有接班人,一定要到头。”可是现在,当同样的问题再次问向赵宗仁的时候,老人窝在沙发里,神情明显疲惫了许多,他不再提一直打官司,而是反问道“出国打,纯败诉还打什么?”
做下和解决定的赵宗仁今年已经86岁,因为被掳去日本时年纪尚小,他仍然可以算得上具有年龄和身体优势。那些他曾经联系过的一百多位劳工,仍然活着的不过五人。宋德祥、陆久文、任有福、贺万起、郑振国……这些他当年骑车去寻找的劳工都不在了。“另外一个比我小2岁的,是当时去日本最小的,也走了。”
据童增介绍,下一步,中日律师还准备与剩下的十几家企业陆续进行交涉。
“未来我们会要求日本政府和日本加害企业一起,向中国近4万名受害劳工谢罪。我们希望日本方面能够成立一个基金会,类似于德国的‘记忆、责任和未来基金会’,对中国二战受害者进行谢罪赔偿。其实日本很多律师、自民党的干部,都是赞同的。这个如果做成了,历史遗留问题才能真正解决。”
对于三菱的和解,小野寺认为值得肯定。“三菱的立场是写明了的,就是不掩饰错误,不重蹈覆辙,克服过去,通过道歉实现和解。但其他的日本企业并没有这个态度,今后也很难会主动变化。”他向《凤凰周刊》指出,劳工方面如果不持续发声,其他日本企业估计不会主动应对。三菱此次和解将会成为一个范本,使得其他企业坚持问题已经解决、没有必要道歉的态度很难行得通。
回顾这26年,童增感慨良多,“这件事的确比较艰辛,但我们要突破一个观念,是不是这事会破坏中日关系?不是的。再一个,是不是影响了国内稳定?也不是。这事情能和解,跟受害者的坚持也有很大关系,也反映了我们不屈不挠的性格。”
在对日索赔的道路上,有好多抗战时的老将军曾对其表达支持,有位当时跟童增说“你有年龄优势”,“那个时候我还不太懂这句话的意思,现在明白了。那些老的都没了,而我还能做这个事情。现在有更年轻的律师加入我们,将来还得靠他们。”
(实习生杨翔宇对本文亦有贡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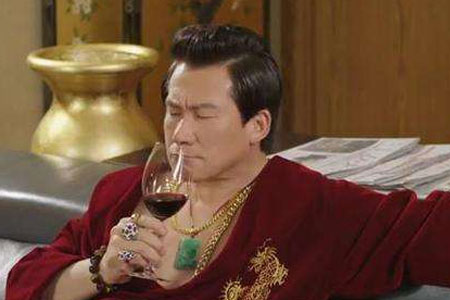








 动物系恋人啊 | 钟欣潼体验爱情哲学
动物系恋人啊 | 钟欣潼体验爱情哲学 南方有乔木 | “科创CP”渐入佳境
南方有乔木 | “科创CP”渐入佳境 魔都风云 | 周冬雨任达华演父女
魔都风云 | 周冬雨任达华演父女







我来说两句排行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