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 隽文不朽之铁证——张爱玲的《异乡记》
(2014 年7 月20 日,星期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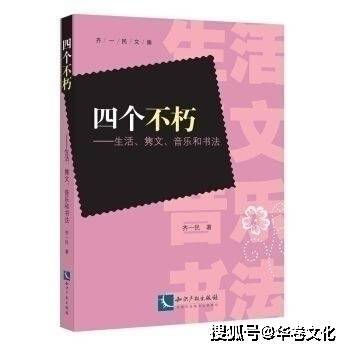 《四个不朽 : 生活、隽文、音乐和书法》 ,齐一民/著,知识产权出版社2015年10月第1版。
《四个不朽 : 生活、隽文、音乐和书法》 ,齐一民/著,知识产权出版社2015年10月第1版。
前天,伴着敦煌到北京的以Z 字打头的“直快”的火车的咚咚、还是在狭窄的上铺,我读着张爱玲的“外集”《异乡记》,我顿感这部三万六千字的短文,就是“隽文不朽”的铁证。
“外集”被编辑出版于作者过世后的这么多年之后,是个“未竟”的稿子,编者朱先生自己竟然说它—或许是个败笔。而我竟然认为,就是这三万六千字本来可能永远难以面世的“张氏遗作”,应该是自从有了文章、文学,尤其是“小说”这种“文”的载体之后,最了不起的一篇,是全人类全加起来的“第一文”。因此,它,肯定是、应该是,也必然是“不朽”的:因为作者的笔法不朽,因为作者的天资不朽,因为作者的境遇不朽,因为作者的聪慧不朽。同时呢,也因为作者的身世和遭际也不朽。这里说的“不朽”,我以为,就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之意,就是不可能重复再现之意。耍笔杆子的,谁能做到不被人重复和复制,谁就会不朽。在同一家书店,我还买了一本同样是“外集”的张氏的英文自传小说的中译本《雷锋塔》,译者是位台湾的当代人,笔法与张氏被熟知的笔法极为相似,但也就是因为这个“极为相似”,更证明《异乡记》是不朽的:《异乡记》我以为但凡是活着的人,就不可能模仿得出来,它是极品中之极品,它唯自己独尊,它丝毫不具备可再生性,它生成于不可被复制之境遇,它被执笔于一只不可再生之“铁腕”,它灌注着大智慧大胸怀大情趣大喜以及大悲之心血的养分,因此,与之相比,《金锁记》《雷峰塔》都全然无色。正是因为了它,我心中的胡兰成之“文”也变得黯然失色和一文不文,也“什么都不是”了。
“不朽”出于比较,奇迹相对于平庸。
《异乡记》之技巧“绝活”在于无处不在的比喻,比喻得绝对出人之意料,而“意料之外”之所以出现,在于作者的一双“天眼”,那双天眼绝非只是“小文人”之眼。是罕见的智者和情圣的“觉悟”之眼,是洞穿之眼。同样一段的那么短的路程,在张氏的笔下,就能变为结合了儒道法外加耶稣基督的全知的“道路”,这条道,既可携你去天国,又能带你下地狱。这是一条不需端头的“没尾巴之路“,因而《异乡记》哪怕是没有结局,哪怕是只有断臀残臂,它也都是完整的。它的尾部,仿佛老子骑驴出函谷,又好比泰坦尼克大头朝下只剩一条船尾巴,它们无论怎样的“结局不理想”,都能给这个世界留下一个永久得不能再永久的美丽以及完满得不会再完满的悬念。
没有悬念的世界是不美好的,没有遗憾的世界是空虚的。
(未完待续)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