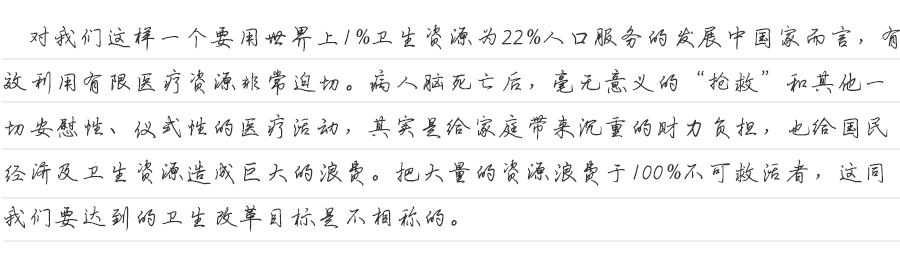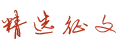文丨全国人大代表 陈静瑜
今年北京的春天格外暖和,我的“两会”时间也更特别。
完全没想到赶在会议间隙,和中日友好医院的同仁一起给三位恰好等到供体的危重病人做了肺移植手术。临走前抽空去看望他们,恢复都不错。这中间器官转运绿色通道助力不少,而它正是我两年前在会上的建议,就从这里说起吧。
2014年起,我就呼吁建立器官捐献转运绿色通道,作为全国人大代表,2015年来京履职时将此建议正式提交。但几个月后的十一黄金周遇到的一次阻碍,让我气愤到在微博吐槽。
当时我的团队拿到肺源后心急火燎从广州回无锡,航班计划8:20起飞,知道路上堵车,我们早已跟南航客服联系,对方也答应配合。不巧的是最终8:05到机场,错过了办理登机手续的时间,值班经理把登机牌收走,坚持不让过安检,而实际上那班飞机9:10才起飞。
救人命的器官就在手里,我们只想快一点、再快一点,反复地沟通、恳求,但现实是只能眼睁睁看着能搭载它马上到达受者身边的飞机飞走。为什么不能特事特办,毕竟生命至上啊!眼看肺源要浪费,我太痛心了。当然也很生气,我喊话说希望南航给一个交代。
南航确实很快给了交代。三天后,南航表示在民航总局出台器官转运绿色通道的相关文件前,将作出表率全力支持我国的器官转运事业。5月,南航成为国内首家开通绿色通道的公司。
随后好消息接连而来。2016年2月25日,国家民航局下发《关于进一步做好特殊航空运输服务工作的通知》;5月6日,国家卫计委、公安部、交通部、民航局、铁路总公司和红十字会总会六部门联合下发《关于建立人体捐献器官转运绿色通道的通知》。
这意味着,从此有了制度保障,上述的无奈状况不会再发生。
到现在,我的感受是绿色通道已经非常畅通。一般团队在得知有合适供体后,会提前12小时跟航空公司联系,紧急状况下五六个小时他们也能做好准备。
比如最近的3月13日,上午我们得知有一例捐献,计划下午取供体,我的团队一早从无锡出发,中午到广州一下飞机订好返程票就和东航联系,3点多在医院完成手术,5:40航班回无锡。团队赶往机场的路上,登机牌已经办好,一到机场快速通过安检,提前上下机。如果在以前没有绿色通道的时候,这不可想象,这么紧张的时间,供体很可能就浪费了。
陆路交通方面的配合也很给力。今年春节,我的团队从临沂走高速公路到济南途中临时向交警救助,绿色通道立刻开通,济南高速交警警车开道,一路引我们到高铁站。而且上高铁也不用提前买票,就近能赶上哪一班就先上车,之后补票。实际已经实现了零转运和无缝对接。
短短一年多,能有这样的改变让我倍感欣慰和振奋。我也再次意识到,只要政府想为民办事,一定可以实现。
坦诚讲,进步是一方面,国内的肺移植事业目前仍机遇和挑战共存。
比如很大一个问题是人们对于肺移植的了解还远远不够,不知道这在国内已是技术非常成熟、可以大大改善生活质量的手术。我收到的求助消息中,病人大多在濒危状态下才决定做肺移植,这时往往等不到供肺就病故,或因错过最佳治疗时间,即使做了手术,术后病死率也高。常有家属在亲人离世后追悔莫及,说如果早点知道肺移植该多好。每当听到这样的话,我都很很痛心。而现实就是大家对此知之甚少,甚至连呼吸科一些医生都不能及时给病人提出肺移植的建议。这需要更多的科普工作,我自己已经通过微博微信尽力在做,更希望有官方支持和大力推动。
另一个我非常期待、也是去年今年连续两次在两会上建议的,是加快脑死亡立法。从器官捐献到绿色通道,我们国内水平已经和国际接轨了,接下来脑死亡立法也是必然趋势。
国际上,脑死亡概念自上世纪60年代提出后,已被医学界广泛接受,脑死亡就是人的生物学死亡,美国、德国、日本等国家也都先后立法,承认被确诊脑死亡就是人的死亡,其社会功能就此终止。我国通过几十年的探索,医疗卫生主管部门也制定了脑死亡诊断标准,经多年实践,目前已为国内医学界认可并用于临床。
有人可能认为我是肺移植医生,希望脑死亡立法就是为了适应器官移植的需求,其实不然。我国有关脑死亡立法的倡议最初是由器官移植界提出,但从推进脑死亡立法和实施相关诊断标准的社会意义上看,器官移植应排在末位。没有器官移植,实施脑死亡诊断标准的进步意义不减;接受脑死亡诊断标准,未必非捐献器官不可。
在我看来,脑死亡立法更重要的意义有三。
首先是维护死者尊严。脑死亡不同于植物人,植物人脑干功能正常的,昏迷是由于大脑皮层受到严重损害或处于突然抑制的状态,因此病人可以有自主呼吸、心跳和脑干反应,少数病人还有望一朝苏醒,而脑死亡已被科学证实是不可逆转的死亡,在这种情况下,人的社会功能已不复存在,应当尊重死者,让死者享受死的尊严。
其次这利于有效利用医疗资源。对我们这样一个要用世界上1%卫生资源为22%人口服务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有效利用有限医疗资源非常迫切。病人脑死亡后,毫无意义的“抢救”和其他一切安慰性、仪式性的医疗活动,其实是给家庭带来沉重的财力负担,也给国民经济及卫生资源造成巨大的浪费。据粗略估计,我国每年为此支出的医疗费用高达数亿。一项调查显示,ICU病人的费用是普通病房病人的4倍,在ICU抢救无效而死亡的病人的费用又是抢救成活病人的2倍。把大量的资源浪费于100%不可救活者,这同我们要达到的卫生改革目标是不相称的。
还有对司法实践需要的满足。脑死亡若不在法律上得到界定,诸多法律问题就难以解决。我国《刑法》许多条款涉及死亡与重伤相应的量刑,但在法医学鉴定中,对于认定脑死亡者为死亡抑或重伤,尚难决断。在《民法》中,死亡是公民民事法律关系产生、变更和终止的原因之一。但死亡的界限标准不统一,确定死亡的时间不一致,可引起遗嘱纠纷、保险索赔纠纷、职工抚恤金以及器官移植纠纷、“不合理”死亡的认定,也直接影响到法律上的继承、婚姻家庭关系中抚养与被抚养、赡养与被赡养以及夫妻关系是否能够自动解除等问题。
关于人们对脑死亡的接受程度,其实在我20多年的临床实践中能发现明显变化。现在已有六七成的家属,愿意在亲人脑死亡后实现其捐献器官的遗愿。
器官捐献的流程很严格,先决条件都是神经内科的医生两人以上、时隔12小时,两次明确诊断无误后,才宣布病人脑死亡。如果家属认可,这个阶段就可以捐献器官,如果不认可,也可等拔掉呼吸机,直至他们看到心脏停跳、认可传统意义上的心死亡后再进行捐献。
我们会向家属介绍,心死亡前器官质量好、救人把握大,你的亲人很快能在受者体内延续生命,而若在心死亡后捐献,有的供体比如心脏就不能用,浪费了爱心。听完区别,他们都非常理解,觉得既然亲人决定献爱心,就要最大化实现价值。这说明加快脑死亡立法是有群众基础的。
同时,多年全国两会上,医学界的代表委员也多次提出,包括我这两年的建议,很多人表示赞同。那为什么迟迟没有落地?主要还是司法部门的观念比较滞后,可能担心由此产生混乱。但我认为立法后不但不会带来困扰,反而可以避免很多纠纷。
另外,我还建议由交通和司法部门推动有器官捐献意愿的人提前登记,比如可学习美国,在驾照上标识“器官捐献者”字样。若发生交通事故后伤者不治,在医院诊断脑死亡、家属同意捐献器官,法医也出具证明的情况下,能快速提供供体而不影响后续处理和赔偿。
作为本届人大代表履职的最后一年,今年我仍希望能再推动一些实际的进步。
巧的是日常工作方面,无锡市人民医院与中日友好医院在会议期间已正式达成合作协议,双方将组成紧密型呼吸专科医联体,成立中日医院-无锡市人民医院呼吸疾病联合诊治中心,未来我们可以更有所为。
医生原本就是一个经常见证生死的职业,尤其作为肺移植医生,跟每一个病人更是生死之交。我的信念是,病者以命相托,医者唯有一心赴救。
当我把两次经历双肺移植的福娃从病床上拉起来下地走路;当我给一对双肺移植过程中相爱的恋人当证婚人;当我看到曾经痛不欲生、家人都不敢靠近的冰冰如今跟孩子一起旅行;当我听到专门等着我开完会的在京病人开怀大笑和唱歌……每一个时刻,都让我充满前行的力量。
你好,我的国。谢谢你为人体捐献器官转运绿色通道所做的一切努力。
你好,我的国。愿我们科学界定一人人死亡时间的进程再快一些。
你好,我的国。愿所有肺病患者轻松呼吸每一天。
你好,我的国。让我们一起期待和创造一个更好的健康中国。
本文由陈静瑜口述,铁瑾整理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