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参与)
人参与)如今美国超级大国的陶醉已然远逝,忧心忡忡的莫雷在书中要传递的讯息,是堡垒的攻破往往从内部精神的陷落开始。这个道理,对于其他国家,想来也适用。
孙 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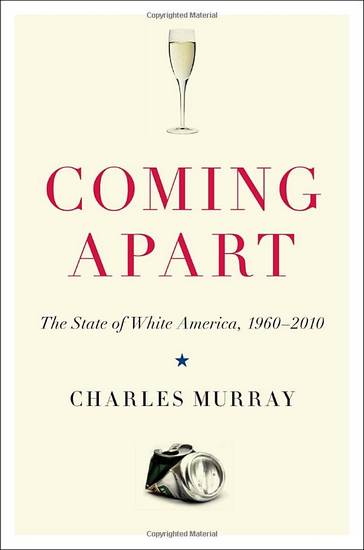
2008年金融市场崩盘,促发了美国经济的严重衰退,至今失业居高盘桓,复苏过程迁延多磨,令失落徘徊的人们质疑,这场病究竟是急性感染呢,还是沉疴的一次急性发作?越来越多的明达之士,无论在民间或在官方,都发出此等疑问。
《金融时报》的美国专栏主笔卢斯(Edward Luce)有广泛的影响力,他在游走美国考察三个月之后认为,美国所患,乃是慢性沉疴,问题具有整体性,而且仍在深化中。据他的测算,2009年起经济止跌回升以来,两年内美国家庭的中位收入的真实价值反而下降了$2000,这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大萧条以来从未有过的。可堪忧虑的是,美国的领导层对此无从响应,甚至不敢直面深层次问题的症结。表面上,是两党政治家各执一偏在缠斗,根子却出在利益正在分化和对峙的民众本身。卢斯提出,要挽回颓势,美国不得不施行大手术,包括推行大规模的“马歇尔计划”。救助的对象,和前次不同,不再是欧洲和日本,而是美国的中产阶层本身。卢斯的悲观看法,以及建议采取的断然措施,从他新近出版的《该认真了下挫中的美国》(Time to Start Thinking America in the Age of Descent)的封面就可看出:一面下垂的美国国旗,末端已见褴褛,中间烧灼的焦黄里,火苗正在展露。
卢斯对时局的判断,由另外一本书得到印证,它就是本文要评述的《分崩离析:美国白人五十年(1960-2010)来的恶化》(Coming Apart: The State of White America 1960-2010)。美国的顶级社会评论家布鲁克斯(David Brooks)对它评价极高,推崇为美国社会政策基础研究的扛鼎之作,是这个领域近十年来最有价值的著作。考虑到布鲁克斯和莫雷(Charles Murray)两个人的价值观和取向立场几乎正相反前者是著名的自由主义斗士(liberal),后者则坚定地捍卫自主行动和采取自由意志主义的立场(libertarian)你不难明白,莫雷的这本新作,实力以及其中揭示的矛盾的深度如何了。
莫雷开宗明义,指出美国社会当前分化的裂隙主要是在阶级,而非人们通常以为的那样以种族或性别为界线。分化得最显著的群体是白人(不包括西裔白人在内)。他用大量人口普查的数据来证明,顶端20%的白人(家庭)和底层30%的白人(家庭)之间的差异在持续扩大之中。造成分野的主要来源是底层群体的“陷落”,和顶层群体的“疏离”。五十年来这些“本质性”的变化有其深刻的根源,有些力量是很难抗拒的,如同冰川的移动或消融。莫雷说他的这本书主要是使人认清,1960-2010年来美国白人两极化的衰败状况,背后的力量则不在书的讨论范围之内。笔者对此的理解是,莫雷的意图,是只谈what,why 的方面点到为止,而how (to correct) 几乎不触及。
从莫雷陈述的焦点,及其摘引数据的侧重,我们很容易体会到他的关注和忧虑,及其呼吁的要点,是美国主流社会国民精神的消退。他的分析范围限制在美国壮年白人,年龄段在三十至四十九岁,时间跨度则为1960-2010年,实际的起点是1963年11月21日肯尼迪总统在达拉斯被刺杀的那天,作者把它看作美国社会分化演变的分水岭。
莫雷依据的数据主要来自十年一度的美国人口普查(CPS),和芝加哥大学的全国舆情研究中心的常年调查(GSS, General Social Survey)。人或人群所属的阶层或阶级主要按年收入的高低的“百分位数”来划分: 即从最顶端的100%th到最低端的1%th来排列。比如说,一个人的年收入在80%th,也就是百分位数80的阶层,是指有(不多于)80%的人的收入在那人之下。依此计算,你的年收入的百分位数如果是7的话,表示最多有7%的人的年收入比你还低。
为了可以客观地横向比较,收入和价格等数据全部转换为统一口径,即以2010年的美元来计值。对于长程的社会-经济现象的研究分析,这个处理非常有用,可以避免许多错误的印象、不必要的误判和谬误的结论。作者明确,按通胀和实际购买力缩水来折算,1960年、1970年、1980年、1990年、2000年的经济数据的货币价格相对于2010年,其乘数分别为7.41、5.61、2.64、1.67、1.26。如果1980年你的薪酬是$10000,那就相当于2010年的$26400,而你在2010年赚了$100000只相当于1960年的$13495。
以此折算,1963年11月的物价相当于2010年的美元价格(乘以1963年的美元指数7.2),汽油每加仑$2.06,鸡蛋每打$3.92,一辆中等汽车$26000,年收入在$100000 以上的家庭不到8%,而超过$200000的家庭连1%都不到。
为了描述易于理解,作者以“双镇记”的形式来讲“阶级分化的故事”。他把处于百分位数80(即80%th,年收入在最高20%的群体)的白人看做是“贝尔蒙”镇的居民,而把处于白分位数30(年收入处在最低的30%的群体)的白人看做是“渔镇”的居民。为了说故事而虚拟出来的这两个镇美国白人分化严重的两个子群体的缩影是以真实存在的两个邮政编码区为蓝本的。贝尔蒙镇实际坐落在波士顿近郊的富人区。2000年那里的家庭年收入的中位值为$124200,百分位数是97,成年人中有63%拥有大学(或以上)学位。渔镇实际坐落在费城近旁的穷人区。在2000年,那里的家庭年收入的中位值为$41900,百分位数是8;成年人中只有8%完成了大学学位。按莫雷的定义,在2010年,能住进贝尔蒙镇的美国人里,有76%为白人,亚裔占其10%;能成为渔镇居民的美国人里,有63%的白人,黑人占了12%,另有16%的西裔。
该书的内容十分丰富,笔者拟就四个方面做简单的介绍:美国白人中产阶级两极分化的概貌;数据和考察方法的一些特色;作者的经历和他的取向;我们能从中汲取什么教益。
莫雷着眼于四个方面:a.婚姻和家庭状况;b.工作态度;c.个人的诚信状态;d.信念和信仰状态。其中 b和 c 是社会公认的两个主要的“个人德性”,而 a 和 d 则是微观层面上的两个基础社会建制。作者强调,它们是美国之所以兴旺起来,并能保持强盛的四根“支柱价值”。
a.美国主流白人社会的婚姻和家庭状况五十年来有令人震撼的沦丧。两个镇的居民(三十至四十九岁)的婚姻状况差别悬殊:贝尔蒙镇的白人在婚姻状态的有84%,而渔镇的白人处在婚姻状态的不到一半,48%。在1960年代,这两个百分比分别为94%和84%。渔镇的白人不结婚或无法结婚的,过去五十年里上升了36%,离婚率则从不到5%上升到了现在的34%。非婚生子女历来很低,不到3%,1960年代后突然崛起,到了2010年接近29%。
从密切相关的另一个数据,孩子和不满四十岁的母亲同住的百分比也可看出:1960年为95%,到2005年只剩37%了。作者甚为忧虑,这些蜕变很可能已经走上了不归之路。
上述的分化趋势也反映在其他三个“支柱价值”上。
b.通过家庭每星期平均工作的小时数来考察民众的勤奋程度,是社会调查常用的一个指标,贝尔蒙镇和渔镇的居民这方面有着明显的分野。从家庭的家长(或配偶)平均每周工作是否达到四十个小时的百分比来看,1960-2010的五十年间,贝尔蒙镇居民的变化不大,从90%微降至87%;渔镇居民的下挫却十分惊人,从81%跌到了53%。
再细看一步,渔镇的妇女每周工作至少四十个小时的比例从1960年的64%只略微下降到2010年的60%。以美国白人男子为其主力的蓝领就业状况的问题,就更形突出了。
c. 用一个负面的数据居民中罪犯的比例,来刻画美国民众的诚信状况这些年来发生的变化。从囚禁在联邦和州立的监狱里的美国成年人数(十八至六十五岁)来看问题,1974-2004年的三十年里每十万渔镇居民中,囚犯平均数从两百十三人剧增到了九百五十七人;每十万贝尔蒙镇居民里的囚犯,则从十三人增为二十七人。
通常人们认为白领在合同财务方面的犯罪倾向较高,实际情况并不尽然。在暴力型和财产型两类犯罪的比例上,渔镇的居民都要超出贝尔蒙镇居民。五十年来两者的差别由数倍扩大到了数十倍。
d.接下来看美国社会的信仰状态。两个镇在世俗化上分别不太大。坦承自己不信神的人,在渔镇,从1970年代的3%上升到了2010年的21%;在贝尔蒙镇,则从1970年代的8%上升到了2010年的20%。不过莫雷认为,实际上不信教的人要远远超过此数:在同一期间,渔镇的居民实际上没信仰约束的,从40%上升到了57%,而在贝尔蒙镇居民中的这类人,则从大约30%上升到了38%。
与此对照,信徒上教堂勤做礼拜的人却在减少:同一期间,渔镇的信徒中勤去教堂礼拜的从开始的55%下降到了期末的40%,而贝尔蒙镇的信徒则从起初的64%下降到了期尾的55%。
美国民众宗教信仰的低落,标志着社会的一个传统凝聚力莫雷称其为“社会资本”正在趋于弱化。
莫雷并没有按马克思主义的标准定义,即以“生产资料的所有关系”来划分阶级,而是结合了物质收入和文化精神生活两个要素来定位。他把过去的富人阶层叫做“老富人”(old-money rich),老富人住的房子可能大一点,多开了几辆大汽车,然而在精神生活的品质上,并没多大不同,也没形成自己特有的价值取向和语汇观念 (value code)。真正的阶级分化,在莫雷看来,是在1960年代以后才逐渐形成的。“新贵”的独特之处在于他们对信息、知识、技能的把握,故称之为知识精英、教育精英或认知精英,他们人数少,素质高,构成了新的上层阶级。区分出等级阶层的一个核心标志,是受教育的时间和品质。莫雷的数据证实,新贵的收入和教育及智商的相关程度极高,几乎可以说,是 “二位一体”的。
莫雷专辟了章节来论述处于新上层的父母是怎样培育他们子女的。他指出,美国妇女生育第一个孩子的平均年龄,没有完成学士学位的是二十三岁,有大学文凭的为二十九点五岁,拥有更高学历的则在三十一点一岁。这样的母亲教养子女,更有经验,条件也更好。其结果,是更悬殊的差别。
书中摘引说,教育良好、素质优异的学生越来越集中到顶尖的大学里。以入学的一个重要标准,SAT的成绩为例,1961年耶鲁大学有25%的学生SAT考分在六百分以下,而五年后低于六百分的只剩下9%了。今天, SAT成绩处于顶端5%(即百分位数95)的美国学生,有20%云集在最顶尖的十所大学里,有50%在最好的四十一所大学就读,有高达74%集中在前列的一百零五所大学里;被那些学府录取的学生,总共才占了全部入学新生的19%。
莫雷特意引用了微软的盖茨先生的一句判断“软件行业说到底不外乎IQ的生意”,来表达他的意图。他想说的也许就是,美国新的阶级分野乃源于“教育和智力的所有关系”。莫雷认为这是一种“自然的力量”,他承认造成的分化将来更难逆转。
莫雷把解析的对象,限定在了成年白人,对演变不追究原因,也不建议纠正措施,显然是为了避免纷争。但是他的主题和指向,必然会激起大争议。事实上他一直是美国最具争议的社会问题作家。1994年他出版的《钟形曲线美国现实中的智慧和阶级结构》,曾撼动了美国甚至欧洲,既是1996年共和党发起的检讨社会福利政策的理论依据,又成了左派强烈抨击的靶子。为了帮助理解,这里对他多几句简介,相信不会多余。
莫雷于1943年出生在爱荷华州的一个爱尔兰裔家庭,父母严谨保守,而他却离经叛道,是个“不良少年”。但他天赋极高,被破格推荐到哈佛读历史。1965年毕业后,他参加和平军到泰国乡村工作了六年,并和替他补习泰语的泰国姑娘结婚,生有两个孩子,十四年后离婚。1974年莫雷在MIT获得政治学的博士学位,论文的内容是关于泰国的乡村治理问题。从泰国返回后,莫雷一直在立场保守的智库机构里做长程研究和数据分析。著作累累,影响深广但争议不断。他是个“自由意志主义者”,并专门著书阐明自己的立场。莫雷对中国和日本的文明评价极高,认为在某些领域里“它们代表着人类所能取得的至高成就”。
至于这本书有何教益,我们中国人能从中汲取些什么,是个更大的题目。注意看一下本书的封面,在高脚酒杯里白葡萄酒的陪衬下,下面那个挤扁了的空易拉罐,显得格外寒碜,不妨引申开来想象。
曾经有大约十五年的时间,美国甚至被称为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单极超霸”,不但军事、科技、经济、规则制定、货币发行,而且文化、观念、语言、价值符号,都是鳌头独占,几乎无人挑战。如今这样的陶醉已然远逝,忧心忡忡的莫雷在书中要传递的讯息,是堡垒的攻破往往从内部精神的陷落开始。这个道理,对于其他国家,想来也适用。
我来说两句排行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