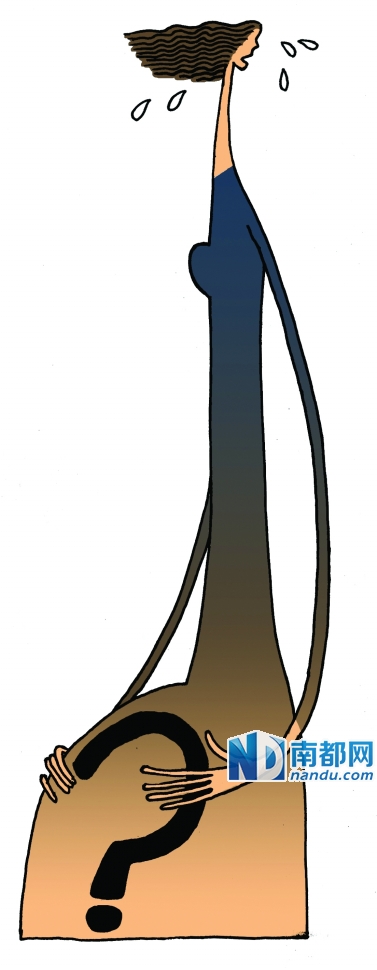
1949年以来,中国经历了两次大的人口政策调整,先有鼓励生育,后又提倡节制生育。除了上世纪50年代初期恢复性增长外,人口经历了两次出生高峰和一次低谷。
两次人口政策调整的逻辑
第一个高峰期出现在1962-1970年,当时强调了人是“生产者”的一面。在“人多力量大”的理念下,中国迎来了第一个高峰期,期间人口出生率年均达千分之36.8。鼓励生育的政策使得生孩子的抚养成本“外部化”。在当时的计划体制下,多生孩有奖励,吃的又是大锅饭,孩子上学、就医基本不要钱,且“公分”与口粮的多少取决于家庭的劳动力数量。这等于私人家庭生孩子由社会来抚养,且多生的收入也跟着增长。如此的制度安排下,给定一个家庭,能多生一定是多生的。这是人口政策上的“公地悲剧”了。
第二个高峰期出现在1982-1990年。实际上是第一个人口高峰期出现的自然结果。第一个人口高峰期出生的男女在20年后进入了婚育年龄。
上世纪60年代的经济目标是“赶超”,目的在快速实现现代化。为此是重点投入重工业,投资源自农业结余,来自农业税和政策性压低粮价。为了降低来自农民的抵抗,更低成本地征收,后建立了人民公社制度,城乡户籍制度被进一步强化,市场被取缔,消费变成配给制。但随着人口的增加,城市人口的就业吃饭压力越来越大,之后有了青年“上山下乡”的运动。
给定当时的制度不变,财富增长受限,人作为“消费者”的一面开始凸显出来,就业吃饭的压力确是越来越大。“节制生育”作为一项政策被提了出来。
1980年9月,中共中央给全国的党员和共青团员发表了一封公开信,号召节制生育。公开信讲得坦诚、直白,说孩子在成人前要用钱用粮,不仅影响家庭的生活水平,也影响现代化资金的积累。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开始了严格的“一孩化”政策。在农村,通过征收社会抚养费,“上环”、引产等政策大幅度提高了生孩子的成本,城里则通过解除违规父母的公职等措施来引导。到上世纪90年代,中国的人口出生率迅速回落。去年中国的人口出生率为千分之12.1,远低于人口数量正常的“新陈代谢”水平。
人口的经济学含义
从上述两次人口政策的调整可以看出,对人口“是什么”的认知是一个重要的约束条件,会影响相应的政策调整思路。“人多力量大”是只看到人作为“生产者”一面,认为整个社会财富的增加有赖于人口数量的增加。这一观点与马克思的“劳动力价值论”不谋而合。在马克思看来,“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劳动时间,财富的多寡跟着就取决于劳动时间的总量了。
而“一孩化”政策则是看到了人作为“消费者”一面,所带来的人口与资源的紧张关系。这源于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在西方被“罗马俱乐部”推向极端,在中国则由马寅初引入而“中国化”。属“僧多粥少”的谬见,大意是在资源有限供给的前提下,必须控制人口数量,才能提高人均享有的资源量和生活水平。
人口是什么?直到新古典经济学时期欧文·费雪的出现,提出了更一般化的“资本”概念后才得到很好的解释。人口是资产,与机器、厂房、资金等一样。凡是能带来收入的都是“资产”。从表面看,“人”这种资产不同于机器厂房,他要维持自身的续存,需要“消费”。但“人”确是人类社会最重要的资产,说重要,是说人所拥有的知识重要。从初民时代的茹毛饮血,到如今在太空中自由穿梭,人类的财富、生活水平不知增长多少倍,期间“自然”还是那个“自然”,山水没变,唯一的变化是人类所拥有的“知识量”。
也就是说,人作为“资产”,其带来的收入大小和财富的增加并不是取决于绝对的人口数量,而是人所拥有的知识量(通俗意义上讲的“人力资源素质”)以及这知识是否受限于“制度”而能否得到应用发挥。“生产者”和“消费者”理论都只看到了“表象”,并进而得出了肤浅的政策结论。
财富及增长是“制度”的函数
在计划体制下,曾发生过现在看似“笑话”的真实故事,国企宾馆内补一个墙洞需要三个人,一人提水泥浆桶,一人拿抹刀,一人指挥;上世纪60年代为了解决就业问题,不得不将数千万城市青年赶“下乡”、赶“上山”,而现在的很多国企却出现“招工难”,为了招到工人不得不出价更高;同样是“人多资源少”的日本,其民众收入水平还要高出中国几倍;这些现象无疑都是对人口的“消费者理论”的有力证伪。
制度变,协调个人和社会从事生产和交易的成本大降,散落在个人身上的知识都能得到有效利用,社会财富大增,个体的生活跟着得到改善,个体更有动力投资于自身的知识累积。人口多不仅不再是“负担”,反而能以其“规模聚集效应”,有助于财富的快速增长和累积。
斯密在《国富论》第一章中,即以造针厂为例,探讨了分工与财富增长的关系。一个工人,若不是分工去做造针的一道工序,而是去做“锉锋”、“钻鼻”等18道工序,一天可能造不出一枚针,而通过分工的专业化运作,每人平均每天可造4800枚。产出大增。分工实际上是个体在单位时间内某一活动的频次增加,使得累积“技巧”和“知识”的速度加快,产出跟着提高。通过交易,并由价格“星光”的指引,每个人可以集中于知识专长处,从而整个社会的产出大增。
跟着斯密又指出分工的深化受限于“市场的范围”,这“范围”除了交易的空间距离外,还包括在同一空间内,可交易对象的密度,即受制于人口规模。斯密是这样写的:
“有许多业务,就连是最下贱的业务,也只能插足在大都市。例如搬运夫,小村落,固不待言,就连普通墟市,亦嫌小了,不能给他不断地工作。散落在苏格兰高原一带荒凉孤寂的乡村农夫,不论是谁,也不能不为自己的家属,兼充屠户、烙面师,乃至酿酒人”。皆因“市场过小,难以给人终身专一业务的刺激”。
也就是说,只要制度“对头”,人口数量的增长不仅不会降低人均所享有的商品和服务,反而有增加的效果。通过分工的深化,社会总财富增加的同时,个体的生活水平也会得到提升。这也被中国近年来的经济增长所证实。
人口规模的“聚集效应”
同时,中国近30年的高速增长不仅为斯密的分工深化理论,为人口的“聚集效应”做了最好的注脚,也从另外两个方向进一步深化了这一理论。
首先是对于中国这类后发现代化国家而言,“学习效应”与人口的“聚集效应”相互促动,效率惊人,并引发了独特的“集成创新”。现在对于“创新”有很深的误读,认为站在全球知识的“顶端”才算创新,否则就是“模仿”、“复制”。这是参照系选择错误引发的“误读”。实际上,只要能找到比原起点更好的生产和交易方法方式,即为“创新”。当中国加工生产和贸易服务的知识与西方相比还有很大差距时,“学习”、“复制”即是最好的,成本最低的“创新”。知识是累积的,学生要变成比师傅更高的高手,先从师傅处学得绝技,是应走的程序与过程。
实际上,恰是被中国的市场规模(“人均购买一美元,即成10亿美元的销售规模”)所吸引,西方各国的厂商纷纷到中国投资设厂,或合资或独资。中国人通过“打工”,学习了来自全球各地的加工生产和贸易服务的知识,然后再把这些“知识”汇集创新,成为比原单一来源地的知识更先进的“知识”,从而赢得了竞争力和市场。中国的“高铁”、“智能电网”是两个典型的例子。这就是“集成创新”。这创新与中国的市场规模大不无关系。若中国地理面积小,市场规模小,不可能吸引到来自全球各地的各业知识。
其次,也是中国经验引发的启示,即人口数量引发的市场规模效应还可以承受更高的“产品合约”或“制度合约”的创新成本,而使得一些“创新”能够产生。同样以高铁为例,像澳大利亚这种地广人稀的地方,高铁开通的收入可能还弥补不了成本,承受“高铁”高额的研发费用实无必要,理性选择是弃置高铁而选空中交通。但中国不同,中国以各种“市场换技术”的手段,集资投入研发,恰是看到了市场规模所带来的商业前景。现在京沪高铁已能实现收支平衡,若中国建成全球第一张通达全国的高铁网,“路网效应”成型,将大大降低人与货物的通达时间,助推中国经济。
权利回归家庭是方向
上面是从一个社会整体的视角谈人口与产出,与财富增长的关系。但既然人口是资产,投入产出有“价”,若无人口政策的干扰,去人为提高或降低生孩子的成本,那生孩子与否或生几个孩子的选择“均衡点”在何处呢?
生孩子的决策权在一个家庭,即家庭是生育的产出单位。人类社会从初民时代的群婚乱交,到血婚、伙婚,再到偶婚制和专偶制,婚约制度的演化是哈耶克意义上的“自发制度”了,目的是为了种的繁衍和“优育”,即要排除血缘交配和乱伦。家庭大致可以说有两个功能,一个是种的繁衍,一个是代际养老的考量。某种意义上,两者可以合并为一。
“家庭”这种组织的“合约”为何会存在?有经济学家从规模效应看,但为了产出的规模效应,不必要男女搭伙成一个稳定的家庭,组成个企业即可。这合约直到科斯提出从“交易费用”看时,才算看清。
人在年幼时不具备生产能力,到年老时生产能力下滑又很快,“家庭”是一个可以平滑个体一生的收入水平,并降低交易费用的“合约”。每个个体刚出生时,饮食起居、升学教育等要有投入,此时不可能向社会借资养活自己,因为存活与否,未来收入如何,能否还款等难以预测,风险太高;年老丧失生产能力时又需要收入养活,也面临同样的问题。人类于是选择了这种父母成年时抚养孩子,而年老时被子女抚养的“隔代养老”“合约”。这“合约”也存在“父不养,子不孝”的风险,但靠风俗伦理的约束,是大致能解决这个问题,不会引发整个社会家庭养老的系统性风险。
至此已然清楚了,家庭的生孩子产出的均衡点即在父母的投入(抚养子女的成本)与产出(养老)的权衡。若多生一个孩子的边际收入大于成本,则选择多生。而实际上,若让父母无干扰地自由选择,他们也不会无止境地多生,而是要接受成本约束的。也就是说,市场配置资源的规律与其他商品和服务没有什么两样,在人口生育这个问题上仍然有效。此说可能让人感情上不大能接受,但却是经济规律。
西方国家在实行“社会养老”后,原有的家庭风俗伦理的约束渐渐弱化,“亲情”变淡,即是明证。实际上,随着孩子的吃穿教育等费用的上升,以及收入的增加,使得抚养孩子的机会成本也跟着上升,非政策强制下,中国现在更多的年轻夫妇的选择是只生一个孩子。
因此,生孩子还是不生,生一个还是两个,这选择要留给父母,留给家庭,由他们自己“计划”即可,因为只有他们才知道什么是最佳选择。“一孩化”的政策到目前已经实行了近30年,两代人的家庭都跟着受到影响,其“扭曲效应”也日益凸显。比如中国的高储蓄率就是与两次人口政策的调整,而呈现出来的一段时期内的青壮年特征有关。“一孩化”政策的调整宜早不宜晚。
南都评论记者 米兰





































我来说两句排行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