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北京昌平区东小口村一带是有名的垃圾废品回收市场,3月下旬已被取缔。 麦田摄(人民视觉) |
| |
制图:蔡华伟 |
如何处理好垃圾?政府部门左右为难,周边居民坐立不安,垃圾处理项目进退失据。
人人制造垃圾,人人讨厌垃圾。垃圾处理设施建设是公认的难题。世界范围内的众多“反建”事例表明,“垃圾之歌”一直充满起伏的旋律。或回收,或填埋,或焚烧,或堆肥……我们丢弃的垃圾,或许比史料更能真实地记录生活。选择处理垃圾方式的过程,甚至可以映射出文明、人性和公共治理的状态。
然而,没有选择的是,日益增长的垃圾产生量与现实的处理能力之间始终存在缺口。垃圾时时刻刻产生,若“处理”跑不赢“产生”的速度,就会“兵临城下”;若处理质量低于科学标准和公众预期,就会造成环境污染、健康损害,甚至伤了民心。
“垃圾问题到底是技术还是社会问题?是理念还是实践问题?是政府还是民众的问题?”因与垃圾结缘而放弃律师职业的北京环保人士黄小山感到困惑。现实中,来自政府、学界、企业、居民等各方的努力似乎无法拧成一股绳。更让人担忧的是,一些由于监管不力造成的负面案例,让居民产生了不信任心理,谈“垃圾处理项目”色变,以致哪里有项目上马,哪里就纠纷不断,甚至发生群体性事件,进而导致项目搁浅。小小垃圾,成为敏感话题。
焚烧还是填埋?二公式英有多恶?究竟如何选址?监管如何有效?垃圾分类与处理到底是什么关系?政府之惑、企业之惑、居民之惑……“惑”不得释,“结”更难解。垃圾问题“脱困”,我们该怎么办?
4月10日凌晨,北京市六里屯垃圾填埋场驶出洒水车向市政井偷排渗沥液,被媒体逮个正着,根据新环保法,或将追究责任人刑事责任。8年前,六里屯要建焚烧发电厂,引发周边居民4年多的反建活动,使得该项目最终被弃。
4月23日下午2点,阿苏卫循环经济园项目环评审批事项听证会在昌平区环保局召开,各方代表进行了5个半小时的讨论。5年前,这个在阿苏卫填埋场建设焚烧发电厂的项目也因居民反建而搁置,今年重新启动。目前,北京市环保局已经拟批准其环评报告。
两个垃圾处理项目的“命运”相似却又迥异,这也是人与垃圾关系困局的缩影。“填埋”与“焚烧”都是目前世界上处理垃圾的主流方式,都会对周边环境产生一定的不良影响,除非在特定条件下,否则难以论定孰好孰坏。与填埋场相比,焚烧发电厂建设更为昂贵,动辄几十亿,但所需面积约为填埋场的1/20,同时垃圾减容能达80%以上,污染排放相对更加可控,还能发电以节约燃煤。
北京这般寸土寸金的特大城市,在老填埋场面临封场但新填埋场无处可寻的现实下,焚烧发电厂似乎是无奈但最佳的选择。但十几年来,针对焚烧的争议从未平息。“二公式英”“邻避”“运营监管”“垃圾分类”,每个“关键词”都能引来众说纷纭。
抵触焚烧发电厂,都是二公式英惹的“祸”?
未知才会带来恐惧
垃圾“脱困”,首先必须“脱敏”。
“垃圾焚烧会产生二公式英,二公式英则会致癌”,这是居民抵触垃圾焚烧发电厂建设的主要缘由。网络上,关于垃圾焚烧厂周边15公里内的癌症发病率远高于周边的言论传播甚广。“百度百科”也如此介绍,二公式英毒性相当于氰化钾的1000倍,砒霜的900倍,一盎司可杀死100万人。
记者在调查中采访了中国科学院环境化学与生态毒理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郑明辉,他是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组织制定《全球二公式英类污染源调查技术导则》的10名专家之一。
“很多信息都是以讹传讹,目前中文网上关于二公式英类的内容80%以上都有错误。”郑明辉表示,在二公式英类总计210种化合物中,只有17种有较高的毒性。由于其对豚鼠的半致死剂量为已知化合物中最低,因此获得了“世纪之毒”的称号。但“最毒”只是针对豚鼠,对于仓鼠、小鼠或者兔子等其他实验动物的毒性则会大大减弱。
“对于人,至今世界上尚未有因二公式英类中毒致死报告,也没有确定因二公式英类暴露而致癌的报告。未知才会带来恐惧。”郑明辉说,目前我国年排放二公式英类约10公斤毒性当量,其中大气排放占5公斤,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的排放量不到大气排放的1%。而人体中存在的90%以上二公式英类是通过肉类、奶类、鱼类等食物摄取。
在科学界,二公式英类是公认的持久性污染物,具有一定毒性、难以降解,可在生物体内蓄积,并通过空气、水和迁徙物种进行迁移。对人类来讲,过量摄入或者暴露的确会对健康造成危害。对此,郑明辉坦承,“轻视或者恐惧都不可取。经过100多年的技术发展,垃圾焚烧产生的二公式英类是可防可控的。如同老虎有可能吃人,但如果我们知道它的习性,就可以掌握防止老虎伤人的办法,比如把它关到笼子里。”
如何“把老虎关到笼子里”?郑明辉表示,可采用措施使垃圾在焚烧炉内充分燃烧和彻底分解,从而避免二公式英类的生成。
由于预见到焚烧会成为垃圾处理的主要方式,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就开始立项制定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其中二公式英类就是控制指标之一。新修订的《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自2014年7月1日起实施,将二公式英类的排放限值从严至每立方米0.1纳克毒性当量,与世界上最严格的欧盟标准一致。
“在最不利气象条件下,并且是在二公式英类最高浓度落地点,按照16纳克的排放值,终身暴露的风险都可以接受。”谈及目前实行的0.1纳克标准,郑明辉说,这绝非一个临界值,而是“放心+放心”的标准。
尽管有了最严的控制标准,仍然没有人会“喜欢”焚烧厂建在自家后院,同时,周边居民还担心垃圾焚烧发电企业会对数据造假。对此,北京市市政市容委固废处处长林晋文表示:“没有什么藏着掖着的,今后垃圾焚烧发电厂的建设,既会有废水废气废渣的排放在线监测平台,还会引进第三方驻厂专业人士,监管生产运营全过程,例如辅料是否足额添加等。”他还透露,今年北京还将研究出台环卫设施监管办法,确保企业完全在阳光下运营。
有环保组织曾诟病北京鲁家山垃圾焚烧发电厂不公开二公式英类排放数据。2月3日,记者来到该厂区中央控制室。11时22分,1号炉膛实时显示温度为1088.6度。一般来讲,达到850度以上,垃圾就可以充分燃烧。由于该厂仍处于环保验收阶段,因此数据暂时没有对外公布。“试运行期间,我们委托国家环境分析中心测了多次,二公式英类排放都远低于0.1纳克,环保验收完毕后会及时向社会公开信息。”技术负责人赵树明说,“我们天天在这儿,如果有污染,我们是第一受害者。”
目前,二公式英类尚不能实现技术上的实时监测,根据生活垃圾污染控制标准,企业对烟气中二公式英类的监测每年至少开展1次,并且公开数据。“尽管不能实时监测,但是可以通过炉温、一氧化碳、残渣热灼减率等间接指标来判断二公式英类的排放。”郑明辉说。
林晋文表示:“焚烧发电厂应当研究二公式英类排放指标的发布机制,包括历史数据和发布渠道,并作为发电厂的规范固化下来。”
“哪儿都不让建,那垃圾怎么处理?”
选址难背后的利益权衡
据北京市市政市容委提供的最新数据,2014年北京市生活垃圾产生量为733.84万吨,日均2万吨。由于厨余垃圾分出率仅为5%左右,因此需要处理的混合垃圾的含水率近60%。这意味着,每天要产生大量的垃圾渗沥液,也就是饱含有机污染物的“垃圾汤”。
“垃圾汤”是臭气的主要来源。“那是一种类似消化不良的蔫屁味儿,直攻心肺,余臭绕鼻,三日不绝。”关注垃圾处理多年、足迹遍布国内外大小垃圾处理设施的环保人士黄小山形象地说。
除了臭气,还有污染排放带来的不良影响,导致无论是填埋场还是焚烧发电厂,如同大街上的公共厕所一般,人人都需要,但都不想其建在自己旁边,即所谓的“邻避”。北京市市政市容委的官员在与居民沟通时,总能听到“不管你们在哪儿建,就是不能在我们这儿建”的观点,可是,他们也很苦恼,“哪儿都不让建,那垃圾怎么处理?”
2009年,北京发布《关于全面推进生活垃圾处理工作的意见》,提出为满足今后50年可持续发展需要,北京将在东南西北方位选址规划4个大型生活垃圾综合利用循环经济园区。目前,北京东有高安屯,西有鲁家山,还有正在开工建设的南宫和大工村垃圾焚烧厂,基本能满足北京市东部、西部和南部生活垃圾处理。但北部地区是生活垃圾处理能力“洼地”,超负荷运行的填埋场在未来几年均面临封场。
在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总工程师徐海云看来,垃圾处理设施建设遭遇了地产利益冲突,“高尔夫球场影响生态环境,国家三令五申严禁建设,还是屡禁不止,盖因与地产利益一致。垃圾处理设施建设大家都认为是必需的,却无容身之地。”
徐海云认为,在现有生活垃圾填埋场选址建设焚烧发电厂应是优先选择。“这是一种改善模式,污染能够显著减少,无论对周围环境还是周边居民健康都是有益的。”他同时表示,若是选址到人烟稀少的地方,不仅运输费用会大幅增加,运输过程产生的污染排放也会增加。
1994年,阿苏卫填埋场投入运行,设计日处理能力为2000吨,设计填埋容量1191万立方米,在承担东城、西城、昌平以及朝阳区部分生活垃圾处理重任下超负荷运行,日进厂量约3600吨。截至2014年12月,已填埋900余万立方米,仅剩两年服务年限。徐海云表示,若能在阿苏卫填埋场基础上建成焚烧发电厂,不仅可以缓解垃圾处理压力,还能将埋藏了20余年的陈腐垃圾陆续挖出并焚烧,从根本上解决填埋场“骨子”里对土壤和水源可能造成的污染问题。
黄小山称自己5年前是个坚定的“邻避分子”,“怕的就是房子贬值”。不过,他认为自己在对垃圾处理深入了解后理性多了。“我去日本考察时,发现他们的焚烧发电厂就在市中心,相当于北京的西单、国贸!在二三十年内,出于无害化的考虑,我支持焚烧。”
除了对于污染的担忧,“邻避”背后是利益得失的衡量。在郑明辉看来,“换位思考”在政府与民众沟通中尤为重要。“我们不能总寄希望于公众自愿牺牲自身利益,还是要利用补偿机制让居民感到利益平衡。”他建议在垃圾处理设施整体预算中列入社区回馈工程这一块,例如在附近建公园、图书馆、游泳池等,或者在电力、热力供应上给予周边居民一定优惠。“国外有的焚烧发电厂修建得很漂亮,里面能够喝咖啡,周边地价一点都没受影响。”
林晋文表示,北京正研究如何在产业、就业、设施惠民等方面促进垃圾处理设施周边区域环境发展,“对于跨区域处理生活垃圾的区县,目前每吨垃圾收取150元补偿费,7月1日起增至173元,用于周边环境的改善。”
同时,“信息公开透明”也是缓解周边居民“邻避”心态的“良药”。当得知北京市环保局受理了关于阿苏卫循环经济园环评听证申请后,周边社区居民认为这体现了政府部门的诚意和进步。
“技术再可靠,运营不可靠怎么办?”
用公开赢得信任
“一想到每天要烧的都是混合垃圾,就感觉剑悬头顶一般。”采访中,垃圾焚烧发电厂周边居民这样对记者诉说。他们始终担心,垃圾含水量太高会导致燃烧不充分。
据了解,目前垃圾入炉前需经过5至7天的堆放发酵来保证热值,技术先进的焚烧炉具有处置混合垃圾的能力,烟气净化设施也能最大程度降低污染排放,不过居民仍然怕“万一没弄好”带来的后果。外地一些焚烧发电厂的负面新闻也加深了他们的疑虑,“技术再可靠,运营不可靠怎么办?”
在郑明辉看来,政府面对信任危机时,不能不作为,更不能逃避,给老百姓造成一种“那东西真不行”的恐慌,一定要把运营监管放在“聚光灯”下,向公众公开与垃圾处理项目相关的信息。其中,对污染控制设施的管理是重中之重。
“高安屯已经装上了长期采样器,北京市环保局可以远程操控,随机设定某个时间段进行采样,再进行监测,从而获得二公式英类排放的平均值。”郑明辉说,“居民担心的二公式英类排放问题靠严格监管可以解决,例如让企业定期公布污染防控中的活性炭、消石灰等原料使用台账,以及飞灰处理运输联单等。”
黄小山则表达了一个疑惑,“我到过国内许多垃圾焚烧发电厂,补贴从几十到几百元的都有。类似的垃圾成分,同样的环保标准,为什么补贴不同?另外,到底需要多少钱才能既保证污染控制,又让厂子有合理的利润?”
据了解,从垃圾扔出家门的那一刻起,费用就开始产生。在小区中,每一户居民要交纳几十元不等的卫生费,从而保证垃圾收运到街道的垃圾转运站,此项工作主要由物业承担。从垃圾转运站开始,费用主要由所在区县“买单”,包括交给北京环卫集团的每吨150余元运输费,以及根据焚烧、填埋、堆肥方式不同而有所差异的处理费。
以焚烧为例,今年7月1日起,北京每吨垃圾的处理费为253元,分类垃圾则为153元。“北京有统一的生活垃圾处理调控核算平台,区县将费用交付到这个平台后,我们再对各个垃圾处理设施进行结算,不够的话由市财政补贴。”林晋文说。
从垃圾焚烧发电厂来看,收入主要由处理费和上网电费构成,以垃圾年处理量100万吨、上网电量2.8亿度来算,平均下来每吨约为435元,但支出则是多方面的。从“三废”处理支出来看,每吨飞灰的处理费为1580元,炉渣85元,渗沥液70元左右。仅飞灰一项,每处理1吨垃圾,就要支出47.4元。
针对污染控制方面支出,记者调查发现,每家焚烧发电厂对于辅料的添加量有一些差异,以消石灰为例,每吨垃圾的投放量从8公斤到15公斤不等。操作人员主要依靠经验以及入炉垃圾成分确定,尚未有统一标准。
根据规划,北京要在2015年达到“4∶3∶3”的垃圾焚烧、生化处理和卫生填埋比例目标。但是这个目标不是“死”的,由于土地缺乏,北京希望能够做到原生垃圾零填埋,即尽可能地将生活垃圾进行焚烧和生化处理,剩下的“炉渣”和“残渣”等再进行填埋。换句话说,按照北京目前每天2万吨的垃圾产生量,除去5%左右的厨余垃圾用来堆肥,北京希望将1.9万吨垃圾实施焚烧处理,仅对焚烧后剩余的炉渣以及堆肥残渣予以填埋。
如此一来,作为危险废物管理的飞灰处理变成了难以回避的问题。据了解,北京目前4座垃圾焚烧发电厂的总设计处理能力为每天5200吨,按照3%的产生率,飞灰日产生量则为156吨,现有能力尚能满足处理需求。随着生活垃圾处理结构的变化,若以焚烧作为主要处理形式,飞灰的日产生量将会达到570吨,年产生量则为20.8万吨,超出北京目前的飞灰处理能力。
“要赢得居民的信任,就需要把每笔账算清楚,并向社会公开。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焚烧发电厂可靠运行。”黄小山建议。
垃圾分类,看似不难可为什么就是做不好?
我们都是第一责任人
就垃圾分不分类,记者随机采访了10名行人。8个人以“没时间”“没人管”“环卫都是混收垃圾,因此没必要分类”等作为没有分类的理由,仅有两人表示会将干湿垃圾分开。
垃圾不分类会带来什么麻烦?
除了产生大量“垃圾汤”,影响入炉垃圾热值,还会污染原本可以回收的资源,同时掺杂在厨余垃圾里的其他垃圾会影响堆肥效果。数据显示,北京市目前每天有3900吨的堆肥能力,但是分出来的厨余垃圾只有几百吨。同时,目前堆肥的品质相对较差,多数只能用于园林绿化。
15年前,北京被列为全国8个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城市之一;5年前,北京开始试点第一批垃圾分类达标小区,目前达3365个,占全市小区总数七成。不过,分类达标考核侧重硬件配备和人员操作规范,投放效果等“软件”占比较小。
据测算,目前北京市民的分类投放正确率不到10%,其中还包括通过垃圾分类指导员实施二次分拣后达到的5%厨余垃圾分出率。在黄小山看来,“混收就不用分类”的逻辑完全错误。“环卫工人打开垃圾桶一看根本没分类,干吗还多此一举分三辆车运呢?”他认为,只有绝大多数人做到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和运输才有意义,政府分类处理垃圾的体系才能建立起来。
26岁的小伙子栗阳毕业后选择当一名垃圾分类宣传员,不管是“线上”的微信、微博、网站信息发布,抑或“线下”垃圾桶旁不厌其烦宣传分类各种好处的“婆婆嘴”,他都能玩转儿。他说,也受到过很多委屈,但是北京“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的垃圾处理目标就是这样踏踏实实、一步一步走出来的。
“其实咱们每个人才是垃圾分类的第一责任人!”黄小山一再说。5年前,他和北京市政府代表团一道去日本考察,去之前不太了解东京有垃圾日历。“我问一位主妇,她家是不是每天都吃生鱼片,她说不,一般周三吃。为什么?因为周四才让扔厨余垃圾。”对比目前国人垃圾分类的意识,他有些悲观,“我们考虑问题往往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强化权利,提出要求,却忽视自己的责任和义务。”
北京已有规定对垃圾不分类的居民进行惩罚。
“罚20元,居民觉得无所谓,同时执法成本太高,难度也太大。”林晋文坦言,“我们应当重视运用经济手段,引导居民进行垃圾分类。”
林晋文所说的经济手段正是向居民收取垃圾处理费,这也是国际上的通行做法,美国、韩国、日本等国家均按实际排放量收取费用。
根据2012年3月1日起施行的《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北京确定要逐步建立起生活垃圾处理收费制度。不过,目前北京生活垃圾处理的费用都由各区县承担,经济压力难以传导到居民身上,对垃圾减量和分类的作用微乎其微。
“目前,我们正在协同发改委等部门研究垃圾处理收费标准,但是仍有一定难度。”林晋文表示,目前外省市试点比较可行的方式是与自来水捆绑收费,可以和水量挂钩,也可以定额,仍会依照多排放多付费、少排放少付费、混合垃圾多付费、分类垃圾少付费的原则进行收费。
被不少“垃圾圈”人士认为是启蒙书籍的《垃圾之歌—垃圾的考古学研究》中写道,在垃圾管理中,似乎道德劝阻远不如收费更具效力。若能按照计量收费,这种经济手段还会影响到商家,促使他们使用更少的包装,设计更易于回收再生的产品。
“100年都未必能解决好垃圾分类。”黄小山说,“因为这需要每个人都意识到垃圾和自己有分不开的关系。谁产出,谁负责,不但承担道义上的责任,还要承担经济上的责任。”
这几年,阿苏卫周边居民王海丽几乎没有扔过厨余垃圾,都用来堆肥。她教儿子从小就做垃圾分类,因为她相信蝴蝶效应,相信先扇动翅膀的这些蝴蝶会带来大的改变。
或许,当下的我们,才是第一张多米诺骨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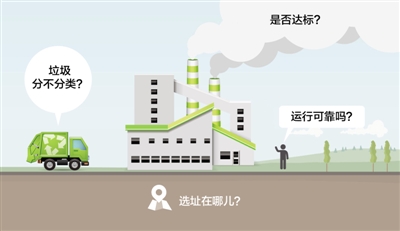










 动物系恋人啊 | 钟欣潼体验爱情哲学
动物系恋人啊 | 钟欣潼体验爱情哲学 南方有乔木 | “科创CP”渐入佳境
南方有乔木 | “科创CP”渐入佳境 魔都风云 | 周冬雨任达华演父女
魔都风云 | 周冬雨任达华演父女







我来说两句排行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