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
拯救美国经济的焦点人物、美国有史以来最年轻的财政部长盖特纳,在《压力测试:对金融危机的反思》(中信出版社,2015年4月版)中,解释了美国如何成功渡过了其政治和金融系统的最终压力测试。
作为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主席和美国总统奥巴马的财政部长,盖特纳帮助美国渡过了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从繁荣到萧条到抢救再到复苏。在回忆录中,他讲述了自己如何做出各种艰难抉择以及在政治上不受欢迎的决定,用以修复一个破碎的金融体系,防止国家经济走向崩溃—他避免了第二次经济大萧条,但却失去了美国人民的支持。
澎湃新闻经授权摘编该书盖特纳对“金融危机是信心危机”的理解相关章节。
金融系统都是建立在信念之上的,这就是为什么“信贷”这个词源于拉丁文“相信”,为什么如果我们相信某件事是真的就可以信赖它(Bank On),为什么金融机构往往自称“信托”。想想一个传统银行是如何运行的,存款者相信银行,将钱存入银行,并且对其还本付息有信心,银行再把钱以更高的利息借出,同时确信不会存在所有人同时要求取回本金的情况。但是如果人们对银行失去了信心—有时出于对贷款质量和管理能力的理性分析,有时不然—他们就会同时挤兑。结果就是大家都奔向银行,就像电影《美好人生》(It’s a Wonderful Life)中的场景,储户涌向大萧条时代的储蓄机构。信心是易逝品,当它开始蒸发,就会瞬间消失,而且一旦失去就很难找回。
金融危机就是显而易见的银行挤兑,是对整个金融系统的挤兑。人们对资金安全失去信心—无论是股东还是债券持有者,无论是机构投资者还是鳏寡孤独—他们从金融系统中暴走挤兑,使体系中的钱更加不安全,也使每个人进一步失去信心。这在历史长河中呈现过多次,无论是富国还是穷国,无论是复杂体系还是简单体系。人类惯于恐慌,正如我们惯于的某种非理性信念(对于房地产、股票或者是17 世纪的荷兰郁金香),造成了泡沫与恐慌交替。而一旦骚动群起,对于个体而言,跟着行动以免被踩踏就是理性的行为,尽管对于社会整体而言,他们的集体行动是非理性的。这些恐慌几乎总是会带来残酷的结果—不仅仅是对投资者和银行,对教师和建筑工人也是如此—决策者几乎总是把他们的境遇搞得更糟。
2009 年年初,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危机中政府应该如何恢复信心?部分答案很简单,尽管令人不快。政府可以支持那些问题公司,消除那些可能把恐惧变成恐慌的因素。为了安慰储户,围城中的银行过去常常把现金堆在橱窗里展示,使储户认为没有必要去挤兑。当政府投入足够的“橱窗里的钱”,就可以减少银行挤兑的危险。典型的例子是存款保险,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用它来应对大萧条时期的银行挤兑。自1934 年以来,政府对银行存款提供担保,所以即使储户担心他们的银行有问题,也不用到银行挤兑而使问题恶化。
当然,罗斯福时代的银行系统没有“抵押债务”、“资产支持商业票据”或21世纪的其他复杂金融工具。在2008 年的恐慌中,被保险的银行存款并没有任何挤兑迹象,但其他各种受到惊吓的资金却夺路狂奔—在数字化时代,挤兑不需要蜂拥到银行门口,只需一个电话或点击鼠标即可实现。2009 年年初,政府已通过问题资产救助计划和其他紧急措施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展示在橱窗中。我们已经增援了价值数万亿美元的金融负债,但金融系统仍然瘫痪着。市场能看到5 枚炸弹,而我们的危机应对措施却显得那么松散,许多政策相互矛盾,投资者和债权人不确信我们是否有能力和意愿来完成这项工作。而不确定性也是所有金融危机的核心问题,没有政府承担风险,金融危机不会消失,私人投资者不会承担那些灾难性的后果。
最明显的反对政府帮助陷入困境公司的理由是,这种做法奖励了纵火犯,表现为两种形式:一种是关于正义道德的说法,即我所谓的“旧约观点”,腐败分子应该受到处罚。缺乏社会责任感者不应该被救助;另一种是关于激励的经济学论证,基于“道德风险”的批判,即如果你今天保护冒险者的损失,他们明天会冒更大的风险,从而在未来制造新的危机。如果你救助纵火狂,最终将遭受更大的火灾。
这些都是有道理的,对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而言,这的确是明智的行动指南。对于一次典型的经济衰退,甚至是有限的危机,企业应该正视自己的错误造成的后果,借给他们钱的投资者也应如此。但是,试图在一次真正的系统性危机中惩治肇事者—通过让大多数公司破产或迫使老年储户接受存款缩水—无异于火上浇油。这意味着将会有更多的银行破产和存款缩水,意味着鼓励储户挤兑。它可以使强者和弱者都处于危险境地,因为在踩踏事件中,羊群都是漫无目的的;这基本上就是金融危机的定义。旧约复仇主义要求迎合当下民粹主义的愤怒,但真正道德的做法是尽快扑灭金融危机中的地狱之火。我们的目标应该是保护无辜的人,即使有些纵火犯会蒙混过关。
我们的做法的确有一些道德风险,批评家,即我所谓的“道德风险原教旨主义者”往往夸大我们对失败冒险者的慷慨。但5 枚炸弹的股东已经承担了巨大的损失;房利美、房地美和美国国际集团的领导人已经出局;雷曼已经不复存在。但更重要的一点,正如奥巴马总统后来所说的,你不应该为了突出在床上吸烟的危险而阻止消防车到失火的邻居家里救火。总统告诉我要专注于灭火。2 月9 日,总统在印第安纳州埃尔克哈特定调了他的财政刺激法案,那里的失业率在短短一年的时间已经从5.2%飙升至19.1%。但是那天晚上,他在就任总统后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强调,经济刺激只是解决方案的一部分。信贷须重新流动,金融系统的信心须重建。
他说,“明天,财政部长蒂姆·盖特纳将会公布一些非常明确和具体的计划。”有记者要求他详细解释一下,但他说要等一天。他已经不能更慷慨,或将期望值提得更高:“我不希望抢财政部长的风头。他打算明天详细阐述这些原则……我将把那个阳光时刻留给蒂姆。”
一支精干的顾问团队一直夜以继日地和我一起制定金融稳定战略,但那时我们只有一个总体框架。我们实际上并不打算宣布计划的具体细节。我的团队在一份内部备忘录中已经预见到这个问题:“首次颁布时许多细节仍然需要保密,这可能会给市场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和波动性。”而且我们还面临另外一个问题:几乎没有同事高度认同我们的战略,甚至包括拉瑞。
但总统用自己的方式表达了对我处女作的信心,甚至敦促白宫记者团来参加我的演说。
“他将是了不起的!”总统说。
我深表怀疑
财政部长们应该树立信心,因为我们的签名出现在美元上。我知道,一家好的剧院—既干净又肃静,会给人一种既可靠又有实力的印象—环境与设施同样重要。但我始终是一个居于后台的家伙。我的职业生涯始终在幕后。在高中时,我就害怕公开演讲。现在,我不得不第一次面向世界进行演讲,第一次使用提词机。而且我也没觉得我的信息有什么了不起。我已经经过足够多的危机,明白这些危机总是云遮雾绕,不可预知。美国人民竭尽全力想得到情况会很快好转的保证,但我无能为力。
撇开剧场,在我令人讨厌的听证会战斗之后,愤怒的公众似乎不太可能会接受我所说的任何东西。我必须说的话似乎也不太可能平息愤怒,其实不管谁说都如此。我会为金融公司承诺更多的政府支持,而这不是一个厌倦了救助措施的国民所希望听到的。我的战略框架在政府内部也极具争议,这一事实表明,其更不可能激发管理当局之外的狂热支持。
我们的战略也非常新颖,这将使其更难兜售。我们不打算先发制人国有化大型银行,我们也没打算让它们破产;两个相似的策略会加速恐慌,但它们却更容易解释这一点。我们方法的核心是做一个“压力测试”,这听起来更像是分析而不是行动。监管机构将钻研大型金融机构的财务报表,测算其将需要多少额外资本来度过一场真实的灾难性衰退,就像医生对患者进行压力测试,看看他们的身体会对艰苦条件做出何种反应。公司随后将要筹集足够的资金填补差额。如果条件差的公司无法从私人投资者那里筹集到足够的资本,政府将强行注入资本差额。
这就是关键。压力测试会是一次更严酷的检验。这将是重整金融系统的一个机制,使银行有足够的资源促进而非阻止增长。我们想给银行一个机会,证明即使没有我们的帮助,它们也可以筹集到度过萧条的现金。即使它们筹集不到资金,我们也不会袖手旁观,坐视其破产,从而触发金融系统彻底崩溃。只要有可能,我们都会依靠私人资本,但如果需要,我们就会动用财政支持。压力测试扮演着一种验伤分类的功能,将重病号与基本健康的人群分类。通过确保金融系统能够承受萧条式的损失,我们认为能够最大限度地避免萧条。
但我还没有准备好提供更多的细节,我们也还没有想出压力测试将如何开展。并且我演讲中的其他部分依然模糊。我将宣布一项买入以前拖累银行的不良资产的新计划,同时我承认计划还没有就绪。我会承诺“制订一个综合的计划以解决住房危机”,但对于此计划,我几乎还没有进一步的解释。我会发出信号,我们不会允许任何雷曼兄弟式的倒闭,这是旨在防止更加混乱的挤兑至关重要的承诺,但这些话被隐藏在我演讲的第26 段内容里。
正如总统曾承诺过的,这将是我的阳光时刻。世界希望看到美国的领导地位,市场希望看到一个可信的计划,公众希望看到他们可以信任的变革,大胆的“是的,我们能”之说已经为总统到白宫的旅程加满油。每个人都希望知道严阵以待的新财长能否胜任这项工作。当我登上财政部装修豪华的“现金大厅”(Cash Room)舞台,在缤纷的旗帜前面,我看起来就像一个在竞选活动前的政客,我知道我的声誉危如累卵。
公平地说,演讲并不顺利。
我前后摇晃,就像乘着孤帆的忧郁乘客;而且一直凝视着提词机,以至于没有直视观众,这显然让我看起来有些猥琐;一位评论家说我看起来像一个商店扒手。我的声音颤抖。我试图讲话有力,但很明显是装出来的。开始演讲不久,我瞥了《华尔街日报》的金融专栏作家戴维·维塞尔一眼,我可以从他痛苦的表情中感到我有麻烦了。总统提高了期望值,而我却正好相反。
在我演讲结束之前,股市暴跌逾3%,全天跌了近5%—即使不算暴跌,但也很不好。金融股全天下跌11%。演讲完毕,我与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的主播布莱恩·威廉姆斯坐在一起—我平生第一次接受电视采访—我看到屏幕上的一个图表:“盖特纳千斤重担一人挑?”威廉姆斯通过引用一名著名财经评论员的评论开始了访谈。
“我听到拉瑞·库德洛说:盖特纳真是一个灾难。”他说,“部长先生,那是我从拉瑞·库德洛那里听到的不错的评论之一。”
库德洛不是一个特例。那时我还没有读到各种评论,但那种“车灯前的小鹿”现象a出现在多个场合。一个演员假扮我,并在《周六夜现场》节目中宣布,我解决危机的办法是奖励第一个打进电话提供解决危机方案者4 200 亿美元。实质性的批评却式微。“应该告诉财长蒂莫西·盖特纳在不确定的时候应该避免的一件事是提出更多的问题。”《纽约时报》编辑部宣称。广受推崇的《金融时报》专栏作家马丁·沃尔夫居然这么分析:“贝拉克·奥巴马的总统职位早已不保?”
这是一次糟糕的演讲,表现得很糟,在不恰当的时候动摇军心。我莫名其妙地既让公众感到我们对华尔街过于慷慨,同时这也让市场感到我们不够大方。民粹主义批评家总结道,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渴望把现金抛给纵火犯;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把我们的计划描述成“银行赢、投资者赢而纳税人输”,但银行和投资者都不知其所云。
“投资者要的是清晰、简洁的解决方案,”一位金融高管告诉路透社记者,“但这个计划却是令人费解的、模糊的、云里雾里的。”
演说之后,一位朋友发邮件给我,里面有一段摘录自泰迪·罗斯福(美国第26 任总统)的名言:“荣誉属于真正在竞技场上拼搏的人。荣誉不属于批评家,属于屡败屡战的人……属于敢于追求伟大梦想,最终取得伟大成就或虽败犹荣的人。”我认为这是一种非常好的永不低头的状态,直到我的邮箱充满了各种类似的表述。另外一位朋友打电话对我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没有什么比这番话更能鼓舞人心。我明白,如果战略不成功,我必须辞职—但更重要的是,经济已岌岌可危。在我演说之后次日凌晨的每日经济例会上,总统郁郁寡欢。“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他问道。
尽管他没有试图把责任全部推在我身上,但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因为我。我无话可说,无能为力。我们才刚开始展示计划的细节,并希望能说服人们相信这是一个很好的计划。我认为如果我们名副其实地完成了计划任务,最终必将重塑信心。但如果计划效果不佳,后果将不堪设想。
历史经验表明,任何金融危机都后患无穷
一项针对20 世纪14 起严重的危机研究发现,平均而言,失业率在受危机影响的国家中跃升7.7 个百分点,大多数乃至几乎所有情况都以银行系统的国有化告终。金融危机对纳税人而言代价高昂。直接财政成本—仅仅是政府为了稳定其金融系统的开支—平均为国内生产总值的10%以上。对于美国,这一成本将会高达1.5万亿美元。
我们目前的危机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巨大的金融冲击影响下,所损失的家庭财富比在1929 年大萧条中所遭受的多5 倍。雷曼兄弟公司危机导致债券息差大幅上涨,约是1929 年恐慌时期的两倍,紧张的投资者大量买入黄金并打算窖藏在自家庭院。股市相对于其2007 年的高点下跌了50%以上。
很自然,多数分析师预计,美国纳税人将付出天文数字的金钱来修复我们的金融系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前首席经济学家西蒙·约翰逊警告说,根据其他国家的经验,政府的预算可能达到1 万亿美元至2 万亿美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份研究估计最后一个价格标签将近2 万亿美元。“从基督诞生起,即使我们每天花100 万美元,到现在也花不完1 万亿美元,”众议院政府监督委员会共和党领袖、众议员达雷尔·伊萨说,“我们失去的很可能远远不只这些。”
但是我们的情况完全不同。
无论是在危机前还是危机中,美国的产出与其他国家完全不同,要比其他国家的情况好得多。那年夏天,美国不但避免了萧条,经济已经开始恢复增长,房价开始稳定,信贷市场解冻,而我们的紧急投资已经从账面上回报了纳税人。
大多数美国人仍然认为我们浪费了他们辛苦挣来的数十亿甚至上万亿美元去救助贪婪的银行。事实上,金融系统已经偿还了我们所有的援助,并且美国纳税人已经从我们应对危机的行为中赚钱了,包括我们在那5 枚金融炸弹的投资中。我们一直很担心我们的资源有限,因此总统的第一个预算曾经包括750 亿美元的第二个问题资产救助计划,但最终我们没有向国会要一分钱。
当然,我们的目标并非为纳税人赚钱。我们的目标是避免美国的家庭和企业由于金融系统破产而遭受灾难性的痛苦。我希望我们可以不必花费国内生产总值的10%就能修复金融系统,但以我认识的每个人都会很乐意支付的财政代价来避免重复20 世纪30 年代的危机。正如我的一个亲密顾问梅格·麦克康奈尔在危机中的重要关头脱口而出,我们离大萧条时代贫民窟的重生不远了。而我认识的所有人,无论是认为我们愚蠢至极的批评者,还是理解我们的支持者,都没有料到,我们那么快就扑灭了金融的邪火,同时又在投资上赚了一票。
2007~2009 年的经济衰退依然是大萧条以来最痛苦的经历。最困难的时候有15万亿美元的居民财富灰飞烟灭,而美国人民谁曾想到在养老金和大学基金这些安全领域的投资也会遭殃,近900 万工人失去了工作;900 万人滑落至贫困线以下;500 万房主失去家园。这些数字的背后,是真实的人民所遭受的真实的痛苦,他们不知道银行危险鲁莽的赌注,他们是无辜的。我的亲朋好友中有的失业,有的失去大部分积蓄,有的目睹自己的企业一蹶不振。即使他们对我依然亲切高雅,但我可以从他们眼中看见,从他们的声音中听到:你为什么不能保护我?虽说经济衰退已避免陷入更糟糕的状况,但对于支付他们的租金或养活自己的孩子而言,却完全于事无补。
的确如此。
美国的失业率升至10%,但不是1929~1933 年大萧条时期的25%。到2013 年年底,失业率已经降至7%以下。但是美国的经济复苏速度比过去的典型经济危机要快得多,而且也要比其他主要发达国家的复苏强得多。2011 年,美国的产出就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而日本、英国和欧元区的产出直到2014 年才恢复。在过去的4 年中,私营部门每个月都录得就业增长,恢复了在经济大衰退中失去的几乎所有880 万个就业岗位。股市已经创下了危机前的新高,危机期间亏损高达5 万亿美元的退休基金都扳回了老本。尽管许多美国人依然痛苦,但已经避免了更多的苦难。
是的,金融系统枯木逢春,再次充满活力。这部分归功于我参与设计和执行的战略,这也是为什么我经常被描述成一个“华尔街的盟友”。《纽约时报》曾经写过一个关于我的有趣的故事,让我浪得虚名—“华尔街内幕交易者”。人们似乎仍然认为我成长在高盛。但在金融危机期间,我们所做的一切没有任何一件事是出于怜悯银行或者银行家的动机。我们唯一的目的在于减少美国民众和世界人民所受到的伤害。
在危机期间,我们所做的很多事情是在正常的资本主义经济中不可想象的,但我们承诺,干预措施将尽可能限制到最低程度。到2010 年年底,美国政府不再拥有任何一家大银行,而联邦政府1984 年接管的大陆伊利诺伊银行—美国第七大银行,与这次危机中的问题银行规模相比绝对微不足道—重归私人控制花了7 年时间。
美国的经济仍在从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中缓慢恢复,失业率过高,收入增长过慢。但美国经济复苏表现优于预期,史无前例,并且好过大多数发达国家。如今,那些曾预言通胀失控、利率飙升、双底衰退、美国政府债券需求崩溃,以及其他关于美国各种恐怖景象的预言家已经成为伪先知。我记得曾半开玩笑地对总统说,批评者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批评者阻止我们推出一个导致经济强劲复苏的方案,另一类批评者相信存在独角兽。
尽管如此,大量不相信独角兽存在的美国人也认为我们把危机搞得一团糟。公众鄙视我们的金融救援措施。出于无奈,在2009 年年中华盛顿的一个晚宴上,总统开玩笑说他需要驯养他的狗—博,“因为盖特纳所需要的一切就是别人把他当作一个消防栓”。而愤怒一直隐忍着。传统思维仍然认为我们牺牲了布衣街的利益去保护华尔街—而华尔街传统的观点认为,奥巴马总统是一个仇视富人的激进社会主义者。危机之后,我们通过分歧严重的国会起草并推动了金融改革法案,这次自大萧条以来对金融规则的最彻底的重大修正,却被普遍认为太软弱,而在华尔街却被认为是存亡威胁。
产生这些感觉我难辞其咎,至少在沟通和游说方面存在障碍。
我对我们旨在拯救经济所做的绝大部分决策感到骄傲,而且我对更好地营销或更好地演讲可以使这些决定受欢迎不抱任何幻想。不过,我从来没有发现如何向公众解释我们在做什么和为什么这么做的有效途径。我们确实挽救了经济,但我们这样做却失去了这个国家的支持。随着危机接近尾声,我建议我的顾问杰克·施维德让财政部编一本白皮书,来解释我们一切有争议决定背后的理由。他笑着说:“听起来不错,你为什么不自己试试?”2011 年,我在白宫举行的晚宴上见到了芭芭拉·史翠珊a,她告诉我:“部长先生,你在电视上总是一副欲言又止、言而不尽的样子。”
我大笑着回答:“你无法想象。”
我现在可以试着亡羊补牢了。
我们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措施依然云遮雾绕,存在误解。而我始终身处核心,从开始到结束,从繁荣到萧条再到抢救复苏,从2003~2008 年领导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从2009 年直到我在2013 年1 月离开财政部。本·伯南克是我在美联储最亲密的同事,也是我担任财政部长后的搭档,是我唯一的另外一位参与了整场战争的主要战友。这使我很清楚地知道,我们如何陷入混乱,我们如何摆脱困境,以及我们如何试图在未来让悲剧不再重演。
这本书讲的是在危机之前、危机之中,以及危机之后我们做出各种选择的故事,并非所有选择都正确,但这也不是一本“要是听我的,就会怎么样”式的回忆录,因为我支持了当初几乎所有的选择。我不可能强迫国会里的反对派和欧洲的对手接受我们的提案,但我在美联储和白宫几乎没有打过败仗。我认为正确和必要的措施几乎都得到了推行,尽管当时我们的权力极为有限。
金融危机的确是对于世间饮食男女的一次真实的压力测试。通常央行和财政部的节奏会唤起战斗机飞行员以前的生活:几个月的无聊生活会被瞬间的恐怖不断打断。我们经历过几个月的恐怖。当全球金融市场处于崩溃边缘的时候,当我们必须在不确定的迷雾中做出重大决定的时候,当我们无从选择但还是不得不选择的时候,我们经历着看似无尽的紧张惶惑。如果我从过去的危机中学会了一件事,那就是谦逊的重要性—关于我们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的能力,以及我们如何安全应用一个简单解决方案的能力。这些都是在大灾变中必须牢记的有用思想,虽然并不令人振奋。
作为危机的第一批反应者所面临的压力,与众多公务员所付出的牺牲相比明显苍白,他们就像真正的第一响应者或我们的海外部队。我们没想获得军功章或者战争费(风险工资),但我们感到了责任的重大。就像我女儿爱丽丝曾经提醒过我的,美国人民至少明白我们在阿富汗的军队是在为祖国而战,但他们对于我们却不那么信赖。
金融危机也是对美国政治制度的压力测试,是对民主能力的极端实时的挑战,即当世界需要创新、果断、政治性的行动来引领时,有能力去引领世界。但至少在最近几年,这些能力还不是我们的力量源泉,关于政治的新闻一般都是冥顽不化和机能紊乱,而我们的干预措施显然没有改善公众对政府或政治的看法。
政治不是我一生的工作,但却给我留下了伤痕,我对华盛顿给我带来的心灵创伤有话说。我目睹了政治舞台上一些令人震惊的行为—自私自利和哗众取宠,无耻虚伪和党同伐异。有时,政治制度的缺陷悲剧性地制约了我们弱化危机和促进复苏的能力。当然,在极度危险的时刻,我们的政治体系还是管用的,两个政党—共和党和民主党—在必要时做到了终结危机,启动复苏,改革体制,获取恰如其分的两党支持以使两极分化的国会正常运转。一群倔强易怒的政策制定者却合作得非常好—争论、苦恼、求同存异,但最终的目的都是为避免官僚化的冲突,提高效率,求得正解。
如今,公众大都对政府是否有能力管理一个“双葬礼”(two-car funeral)持怀疑态度,年轻的美国人都不愿意进入公共服务领域,而这无可指摘,好在我们的系统通过了压力测试。
我希望这本书将有助于回答一些仍然萦绕着危机的问题。为什么会发生?我们如何使之发生?我们如何决定该救助谁?为什么我们不对银行实行国有化,或者让更多的银行倒闭?如何在使左翼相信我们是华尔街的同伙的同时,让华尔街感觉我们是穿着西装的切·格瓦拉?为什么我们没有对住房市场干预更多(或更少)?为什么我们没有得到更多(或更少)的财政刺激?经济为什么不再蓬勃发展?雷曼兄弟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当初我们不把危机消灭在萌芽之中?
本书不是讲述金融危机的流水账,这件事别人已经做过了,虽然他们的故事大都止于2008 年。这也肯定不是奥巴马总统第一个任期内的经济政策史,而是关于一位政策制定者对导致危机的各种事件的深入观察、危机期间的关键选择、危机的余震效应以及体制改革斗争的历史。我希望本书可以载入史册,同时纠正一些历史误会,并还原危机的本来面目。
我写这本书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金融危机危害巨大,这也不会是最后一次。然而,美国却没有一支常备军来应对金融战争,没有参谋长联席会议,没有战争学院,也没有剧本。尽管所有金融危机都不同,但它们有很多共同点,这次极端情形的经验教训可以对政策制定者和公众应对下一次危机有所帮助,我希望本书能够成为指路明灯。
我从刚刚进入财政部帮助前任部长罗伯特·鲁宾(Robert Rubin)和拉瑞·萨默斯应对一系列新兴市场金融危机时的经验教训说起,处理本次危机的许多方法思路均源于此。然后,我将讲述泡沫破裂前我在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作为金融监管者之所见、所做和所误。在此期间我犯过错误,但绝对不是大多数人所以为的那样。这是自大萧条以来的最为严重的一场危机,自2007 年爆发,于2009 年结束。故事的核心,将是我对于这场危机的看法—不仅包括我在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就已经开始实行的金融工程,也包括关于刺激政策、住房市场以及奥巴马时代宏观经济的争论。
截至2009 年年底,最严重的危机在美国终结。但我仍然面临一些挑战。华尔街改革争斗尤酣,我们努力出台一些金融规则,可以使未来减少危机频率及降低其恶果。然后欧洲开始崩溃了,我在剩余任期内一直敦促欧洲人更加积极地解决他们的危机。我们也开始了一系列关于财政路径的预算谈判,但差点儿毁于一旦:国会中的共和党对手迫使美国政府财政违约,这将是一个真正的末日场景。
这些争斗都是大危机的回声。但在我描述这一切之前,我应该解释一下我是如何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刻最终胜出的。我与伯南克和拉瑞·萨默斯不同,他们都是学者,我也不是汉克·保尔森和鲁宾之类的华尔街大亨。我非常偶然地经历了这段历史。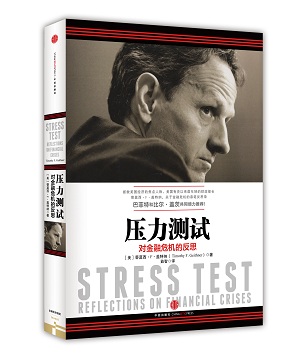
版印次:1-1
开本:16开,456页
定价:58元
出版日期:2015年3月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动物系恋人啊 | 钟欣潼体验爱情哲学
动物系恋人啊 | 钟欣潼体验爱情哲学 南方有乔木 | “科创CP”渐入佳境
南方有乔木 | “科创CP”渐入佳境 魔都风云 | 周冬雨任达华演父女
魔都风云 | 周冬雨任达华演父女







我来说两句排行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