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任剑涛 |
“屈从”是中国高等教育和基础教育的共同特点
搜狐文化:您认为中国教育现在存在哪些问题?结合您个人的经历来说,您有哪些教育理念?
任剑涛:中国的教育定位明显有一些弊端,主要是认读性、机械性的教育占据了基础教育的绝大比例,这导致小孩的人格教育、责任教育、规则教育、社会教育基本上缺席。这些教育一旦缺席,小孩的人格成长就有问题:他们对未来没有打算,在家庭中得到父母的宠爱,对同学、老师、社会、陌生人、公共规则缺乏认知。
我在同代人里算是罕见地接受过完整教育的人,生活在毛时代,我们从小的教育都很随意,基本上就是玩,所以我教育小孩也基于个人经历,便抓得不紧。毛泽东当年也说,学生考试不是紧要的,“不会做,抄一遍”,学习以政治和玩耍为主。我们是基础教育被荒废的一代,改革开放之后上了大学,之后进入研究院,才逐渐意识到教育可能存在问题。不过荒诞的教育体制结下奇特的果实:我们这代人可能因为儿时教育被荒废,所以也没有过分讹诈学习的兴趣和积极性,以至于壮年还有一些学习积极性。
这跟我太太对教育的认知就很不同,她认为小孩的教育必须抓紧,她自己从小就是从各种兴趣班学出来的。现在我们两人在一起教育小孩,出现了两种畸形:一是像我这样,从来不给女儿报语数英课外班,报的全是玩的,比如钢琴、舞蹈、网球、游泳。舞蹈老师对我女儿说,“你身板硬,不适合学舞蹈”。我则跟孩子说,“你告诉老师,我们以后不吃舞蹈的职业饭,只是来学一学,玩一玩而已”。游戏性教育或是博雅性教育,都有保护小孩学习积极性的效果,认读教育、人格教育、社会教育和政治教育要并进。
搜狐文化:你在一次演讲中提到,中国大学教育存在“屈从”的情况,那么在中国的中小学教育中是否也存在类似情况?
任剑涛:整个中国教育的规划是一以贯之的。因为报道大学的消息多,所以大家盯高等教育盯得特别紧,中国高等教育在资源获取方面也确实远远超过基础教育,但教育的屈从恐怕是共同特点。
在国家布局上,政治性内容比重很大,从幼儿园到博士后纹丝不动。这种教育会让小孩的国家认同比较强,因而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情绪比较强烈。今天的流行词汇“小粉红”,就是这种教育布局的后果。但政治内容充斥教育过程,也会导致学生的综合性成长和发育不足,对社会缺乏认知,对规则缺乏尊重。长期如是,父母也习以为常,似乎小孩没有进行独立判断的必要。
另外,知识的传授性教育占了重头戏。这种教育模式的优势是,中国学生在基础教育中的能力,在全世界范围内比,都是很强的。有一部BBC拍摄的纪录片《中国老师在英国》在网络走红,中国的中学教师到英国中学去教书,有人讲中国的虎爸虎妈变成虎老师,英国人不接受,一时人们无情抨击中国教育。但后来剧情反转,英国方面反而认为中国的虎老师好。因为英国的中小学生学习不努力、不认真,知识的认读效果比较差,尤其是数学能力跟中国学生没法比。不论在英国、还是在中国,基础教育阶段的机械性识读,即非创造性的知识传授,都是主体。学生在这一阶段尚处于社会化的早期阶段,自主和自控能力比较差,一定的强制性教育手段似乎是必要的,对其进行诱导性教育,恐怕只是一个教育乌托邦。但过分强制的识读教育也会让学生的创造性能力和学习积极性,受到双重抑制。
中国的基础教育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成系统。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孰优孰劣,双方各有判断。我曾经跟一位国家知名重点中学的老师,陷入过一次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间的相互指责。
搜狐文化:具体是个什么情况?
任剑涛:大家都说中国大学办了几十年,没有培养出世界级的杰出人才。原因何在?我对他说,是中学教坏了学生,机械性的识读教育占了中学教育绝大部分份额,学生被训练成绵羊,只是听话,没有创造力,且消耗了学生的学习热情和知识创新的愿望。
这位老师反驳说:“恰恰是大学教坏了学生。你看中学生被我们训练得多好!听话、忠诚、认真,高考阶段就开始筹划未来的人生,心无旁鹜,全情投入。教师、学生、家长三方协力,配合得很好。但一进入大学,师生关系就比较畸形,学生要找老师都不容易。尤其在985大学,招的都是尖子生,但就是这样的尖子生一进去也被分成三六九等。大学看重的专业教育,报废了中学的宽口径基础知识,结果把学生教成专业废物。”
这次争论,使我开始反思,为什么中学老师和大学老师双方积怨这么深?这两者本不该陷入互相指责。民国时期,大学老师也当中学老师,中学老师也随时可以跳到大学任教,双方之间有一个旋转门制度。按现在的教育体制,这种流动几乎不可能。
人大附中2016年新招聘的十多个教师中,有海外的博士,有国内985大学的博士,硕士就不用说了。大家一再说这是浪费人才,其实这不是人才的浪费。基础教育需要相当强的专业支撑。我们的教育从幼儿园起,就以识读教育为重点,人们以为只是到了大学才以创造知识为重点。但合理的教育安排,实际并非如此。识读性的教育在大学照样是核心,没有厚实的知识传授,哪有知识的创造?而中小学教育重视的听话、忠诚、爱国,这是高等教育也需重视的,尤其在中国,但凡涉及教育的“政治红线”,谁都不能碰。可见,大中小学教育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是完全隔绝的。旋转门机制,确实有利于合理的教育系统运行。
搜狐文化:那么中国教育布局的第三个特点是什么?
任剑涛:第三个特点,就是中国教育体制的安排,完全是围绕着实用主义目的来展开的。实用教育本身没错,但是将使用换算成算计,就很糟糕,为钱理群所批评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其实就是一种精致的算计者。
即使是“学以致用”,也需要在技术创造性上体现出来,中国教育目前连这一点也没做到。李克强总理讲,中国现在的工业水平之低,连一个合格的圆珠笔笔芯都生产不出来。这本是第一次工业革命就该解决的问题,而我们今天号称在进行第四次工业革命。为什么现在大学有些工科生愿意读理科、理科生愿意读文科,文科生又乐意读时髦的金融、管理?原因在于好谋生、就业方便。加之中国金融资本的收益远远超过实体经济的吸金能力,这给大学生做出非常糟糕的示范。大学生以赚大钱为目标,在这样一种低级实用主义价值观的驱动下,个人兴趣、专业偏好、天赋能力等等,都被实用密密实实地掩盖住了。
从空谈理想到理想变为笑柄:教育需重构接近现实的乌托邦
搜狐文化:你刚才提到一个词“教育乌托邦”,鉴于中国教育的现状,这是否是对中国集体式幻觉的一种警告?
任剑涛:在某种意义上,每一种教育体制背后都有相应的教育乌托邦。差异是,这个乌托邦的可行性有多少。乌托邦理念本身其实是宝贵的,完全缺乏乌托邦的想象,教育就没有愿景。教育乌托邦和现实之间的距离要相对较近,换言之,教育的目标是可期待、可实现的。
搜狐文化:也就是说要构建一个健康的、符合现代性的教育乌托邦。
任剑涛: 我们不谈人类最终能实现什么目标,只说我们这一代人能实现什么目标,这是教育乌托邦的实在性体现。具有可能性与可行性的教育乌托邦,只能通过一代一代人、一个一个的个体,在组织化的社会生活中去兑现,这是现代教育谋求实现其乌托邦理想的现实途径。否则,教育完全堕化为虚幻教育,最终反转导致教育的极端实用性和功利性,让急功近利彻底败坏掉教育。中国教育从文革式的虚幻乌托邦落到改革开放之后的急功近利,也就是从一个必定幻灭的乌托邦落到极其冰凉的现实平台,落差一大,让人惊诧:前者的教育模式极尽理想,大家都空谈理想;后者是谁谈理想谁就变成笑柄。
搜狐文化:是否可以说,中国的教育改革,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重构中国教育的乌托邦?
任剑涛:对,一定是这样的。中国一定要突破教育政治化、意识形态化的瓶颈。教育的政治功能是重要的,现代教育还是以民族国家为依托的,在一定程度上,国家理念、国家认同、爱国主义是需要引入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的,但是要严格限定它的规范含义。教育的政治冲动是一股太强的力量,这也正是中国出不了世界级大师最深层次的原因。具体落实到教育的改革、教育的未来,大家都不约而同地尝试用教育的行政问题来搪塞更深层次的问题。在我看来,教育的政治化问题,才是中国教育最重要的问题。
中国教育的政治愿景,需要重新谋划。今天,教育的政治愿景,还停留在危机状态下做出的安排,即那种为了谋求国家独立、走出被动挨打、告别列强欺辱、争取民族解放状态下的教育想象。教育在和平时期的建设需求、未来发展、人类使命,都没能真正摆到教育的政治台面上。
教育体系的整体想象力需要重塑
搜狐文化:除了中国教育的政治想象要重塑,中国教育体系的整体想象力似乎也亟待重塑。
任剑涛:没错,教育结构要重新检讨。首先是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的安排问题需要再构思。政治化、传授性和实用化教育充斥了从初等到高等教育的全过程,而初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分流又不太清楚,这是需要解决的大问题。现在教育部已经废止了985计划和211计划,重塑高等教育的进程已经开启,但受制于国家教育的行政化布局,一旦这种重塑服从于中央政府拨款机制,各方的角力可能又变成了一场行政博弈过程。到最后,烂尾的可能性不是没有:一流大学的队伍越做越大,一流水平指标却降得越来越低。
除此之外,还要改变教育的知识结构。中国教育的知识结构非常陈旧,而且有明显的高深知识下移的特点,比如高中就学微积分,而在发达国家从大学才开始学。知识的下移造成本来应该以兴趣培养和知识教育为主的初中等教育,变成繁重的知识传输教育。繁重的知识传输对基础教育的老师和学生都造成巨大压力。大学知识教育方式也是陈旧的:教材占据了不适当的重要位置,而教材建设过于重视稳定性,成了政治和利益相互支撑的一种状态。大学教材普遍跟不上知识发展,且习惯性地由党政领导主编或者组织。尤其是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习惯于请耄耋之年的老专家来评审教材。他们确实是著名学者,但毕竟年龄不饶人,即便是人文社会科学,当下的发展也是日新月异,知识快速更新,何况是理工科的?理工科的院士,对整个大范围学科知识的控制能力和资源吸取能力,导致了明显的学术保守倾向,一定程度上妨碍了科学技术的进步。
我们还要改变教育的评价方式,在中国的教育中,老师是绝对主体,学生就是接受人群。虽然各个学校在教师评价标准里,想方设法提高学生的主动性、参与性,但在总体的制度安排下,因为没有平等机制这个前置条件,要学生对老师提出有效要求的可能性不大。发达国家的大学生创意如此活跃,是因为学生和教师在一起讨论科学问题的时候完全平等。不像中国,年资还是学术讨论的自然秩序,就像人们形容的,在历史学界,90岁的没发言,80岁的不敢讲;80岁的没讲话,70岁的不敢讲,等讲到20岁的时候,会议该结束了。我自己对此有些警觉,常说“师生一久成兄弟”。但实际上我也很难跟我的学生平等讨论问题。大环境如此,养成了教师的霸主行为。犹如网民常说的,中国的小暴君习性遍及全社会,只要有点支配能力,相对弱势的一方一定要接受支配,否则就有你好看。
中国家长宁可子女输在终点,也要赢在起跑线
搜狐文化:体制内的教育愿景固然需要调整,整个中国社会尤其是中国家长的教育愿景似乎也相当成问题。
任剑涛:中国父母望子成龙之心过强,所谓“不要让子女输在起点上”即可佐证。我有一个玩笑性的说法,这些家长过于看重起点,其实“他们宁愿让子女输在终点上”。在国内,好像一个学生一旦考上大学,父母就对子女完全放心了。殊不知,考上大学才刚开启了子女发展最重要的第一个人生关口。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是在父母和教师的全方位约束下展开的,学生并没有以一个独立的个体面向社会。而读大学,哪怕是同城走读,也基本上脱离了父母的监控和老师的干预,他们开始成为社会人,独立思考在大学里怎么学习,怎么处理同学和师生关系,怎么在社会中生活,怎么遵守规则,可以突破哪些规则进行创新……解决这些问题,都需要他们勇于试错。
对人生而言,起点不利当然是严重的不利,比如出生在北京市的小孩,他的高考如愿机会远比陕西窑洞出生的农村小孩多得多。这是不公平的。但是教育绝不只存在一个起点问题,截止人生的终结点,才能最终判定他所受的教育是成是败。
同时,传统观念的作用也不容小觑,中国人期待靠教育光宗耀祖,自古至今都是如此。
中国把光宗耀祖的理念当成社会稳定器。7月,学校都进入暑假。我对中国教育问题的感受也变得特别强烈。因为暑假,无数望子成龙的家长都纷纷带着读小学或中学的孩子来我任教的清华大学参观。我曾经问家长,你们花这么多钱,在如此炎热酷暑之季,到清华来干什么呢?父母很坦诚地讲,我们的一生已经没有希望了,一切希望就放在小孩身上,为了他一切都舍得。我一看家长只有三四十岁,马上悲从中来。如果每一代人都在壮年或中年时代,最有朝气最能发展成为中坚力量的时候,就放弃了自己的人生,而把希望转移到下一代身上,下一代以同样的逻辑再转移到下一代身上,这将造成人力资本怎样严重的浪费?更将造成怎样的传递性人生悲剧?
代际互害:40后50后是在极不健康的环境下成长的一代
搜狐文化: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下,又怎能期待出现杰出人物和大师?
任剑涛:我记得一个报道,说有一个华人,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毕业后二三十年都只能在大学任低级别教员,不得不打零工补贴家用,到了快六十岁时,终于解决了一个世界性数学难题,成为全球著名数学家。这在中国是不可能出现的奇迹。在国内,20多岁大学毕业,尚无法自立,父母出钱给小孩买房,希望他将来能挣大钱赡养父母。双方的迫害,由此开始;到了三、四十岁“三代同堂”,上有老、下有小,三代相互干扰、互相迫害,彼此都无法实现自己的人生意愿。今天有的人喜欢想象三代同堂家庭的无限好处,殊不知核心家庭的普遍生长,才是现代硬道理。
搜狐文化:这实际上造成了一种互害模式。
任剑涛:试想,民国早期,为什么家庭革命成为社会革命的先声?家庭价值当然极为重要,孝道也极为重要,那是社会规范注定了的事情。但是每个个体都有自己的价值、有自己的天地、有自己的人生责任。因此,需要指出,父母必须承担起父母一代的责任,这是父母的义务注定了的事情,但这并不直接构成子女孝顺的理由。子女尽孝,是子女一代应恪守的社会伦理,但这并不构成子女无条件服从父母的理由。只有为人父母的一代清楚这一现代规范,才能给子女创造真正健康成长的空间,拓展子女成长的道路,否则就是在为害自己的子女。
40后、50后一辈,逐渐进入养老的状态。据说当下中国社会超过60岁的老年人已过两亿。这些出生于40后、50后的两波人,正是老龄化人口的主体。他们正在塑造中国当今的老龄社会氛围,这一波人最大的问题是,他们是在极不健康的环境下成长起来并定型下来的。40后基本在建国时期成长,政治热情极其高昂,对子女的政治要求也极为严格,使子女也在政治畸形的环境中长大;50后完全成长于中国废除现代正规教育的时代,他们所受的教育是很粗放的,对外,当年最高领袖支持“不学ABC,照样干革命”,成为全国废除英语教育的根据,因此对世界大势不清不楚,但指手画脚的热情却不因此稍减;对内,以学工学农学习解放军取代了知识教育,现代知识的极度匮乏令人触目惊心,但这也不稍减他们好为人师的冲动。70后、80后两波人,在这种代际结构中,很难接受健康的代际教育。
对于中国教育的问题,该官方解决的官方解决,该社会解决的社会解决,该教育部门解决的教育部门解决,该受教育者和教育者要承担的责任由他们自己承担。还教育部门作为一个社会分工部门的本来面目,不要期待教育解决中国一切问题,这是让教育相对轻松上阵,收获优良教育效果的必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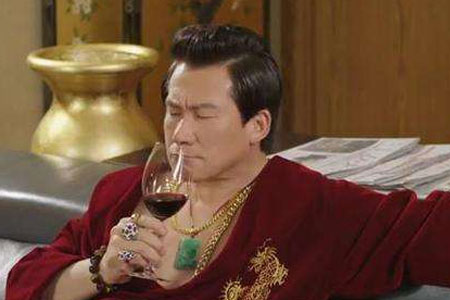








 动物系恋人啊 | 钟欣潼体验爱情哲学
动物系恋人啊 | 钟欣潼体验爱情哲学 南方有乔木 | “科创CP”渐入佳境
南方有乔木 | “科创CP”渐入佳境 魔都风云 | 周冬雨任达华演父女
魔都风云 | 周冬雨任达华演父女







我来说两句排行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