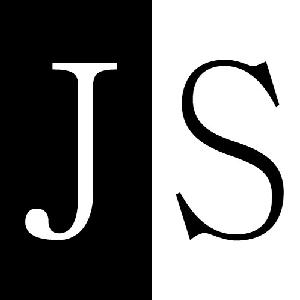从大学路望去老城区一角,2002年
从目前中国一些摄影家的工作方向来看,以一个社会工作者的身份而不是摄影家的身份,从社会学的角度来从事摄影工作已经成为一种新的趋势。人们已经不再过多地迷恋于那种徒慕虚名式的得奖,也不再满足于那种按下快门就走的浮躁浅薄的工作方式,而是审慎地选择一个村庄、一条街道、一条河流、一类流动人群、或者一种人文景观作为观照对象,然后沉下心来,积数年之工夫,一方面大量采集图像资料,一方面通过长时间的调查访谈,取得大量一手的文献资料,然后集结成一个内容丰厚的有一定学术纵深和持久价值的文本。
——刘树勇
01
历史中的社会学图像
1999年秋,因所在学院的中文系学生开设“文化人类学”、“社会学”和“民俗学”课程的原因,我带一个班的学生到青岛郊区滨海的一个小村子中做为期三周的田野调查作业。其间数次到市区办事,在摄影家吴正中的家里,我看到了他近十年来拍摄的有关青岛老城区的照片。其规模之完整,影像之朴素,令我十分惊异。正中带我在他拍过的一些街道和院落中转来转去,边走边向我指点介绍这些地方的由来和现状,这个那个,如数家珍一般。 看到正中那种质朴无华的工作方式,那种极为单纯而且平淡的心境,以及足可以建立一座老青岛城区影像档案馆的数量巨大的照片和文献资料,我意识到,事实上他正在做一种类似于社区研究的摄影记录工作。
辽宁路、益都路、大港码头区域,1999年
从摄影的角度来说,这种观看和把握外在世界的工作方式,图像形态以及形成的规模和系统性,甚至摄影家从事摄影的心情,已不同于以往我们熟悉的那些用于新闻传播的、个人情感表达的或者是视觉语言体系建设的摄影形态。这些照片的最终结果是构成一个社区、一类人群、一种经济形式、或者是一种人文生态的视觉整体。而且其价值也已经无法在摄影范畴的内部来进行判断,而只能在现实社会与历史文化的意义和平台上来界定了。
我把这一类照片的功能称作是图像的社会学功能。用作社会学目的摄影当然并不是从现在才开始。历史上大量由摄影家拍摄的图片曾经产生过非凡的社会影响,并被后来的社会学家们广泛地用作研究的佐证资料。比如《纽约民报》摄影记者雅格布·里斯(Jacob August Riis 1849–1914)于1887—1892年间拍摄完成的纽约贫民窟的系列照片,以及出版的《被社会遗弃的人们》和《贫民的孩子》两本书,直接影响了纽约州州长罗斯福作出决定,并最终改造了这一社区。再比如法国摄影家尤金·阿杰特(Eugène Atget 1857-1927)从1898年至1927年间拍摄的有关巴黎城区各种景观的近万幅图片,成为后来研究这座城市人文生态的社会学家们极为珍贵的图像档案。
雅格布·里斯作品
尤金·阿杰特作品
也有一些摄影家自觉地去以一个社会学家的姿态和专业素质去从事这种意义上的摄影纪录活动,比如本身即是社会学家的路易斯·韦克斯·海因 (Lewis Wickes Hine 1874–1940)出于1905年开始拍摄的有关美国欧洲移民劳工生存状态的照片,并从社会学的专业角度进行系统化的研究。特别是他有关移民童工悲惨境遇的研究及拍下的大量触目惊心的图片,最终迫使国家议会通过了旨在保护儿童生活权益的《儿童劳工法》。上个世纪30年代中期,由美国农业保护管理局委托多罗西娅·兰格(Dorothea Lange 1895-1965)、沃克·埃文斯(Walker Evans 1903-1975)、 阿瑟·罗特斯坦(Arthur Rothstein 1915—1985)等一批摄影家,辗转全国各地拍下的有关经济大萧条时期美国农业状况的大量照片,尽管后来的人们更多的是从摄影的角度去阐述那些影像的价值,但其最重要的意义却在于,这是一次由政府出资组织的社会学意义上的大规模的调查作业。由摄影家拍摄的数量巨大的图片和由另外一些社会学家撰写的调查报告相互印证,成为政府进行农业决策以摆脱经济大萧条的重要依据。
沃克·埃文斯作品
多罗西娅·兰格作品
但是,更多的社会学研究活动仍然集中于文字描述、逻辑分析和数字统计,而缺乏大规模完整的图像采集和视觉化的实证调查。二、三十年代,以研究都市社区闻名于世的美国社会学芝加哥学派主持研究了芝加哥逐渐都市化的过程,用来说明美国现代城市的结构和动态。在研究过程中,这个学派以芝加哥市内的犹太人聚居区、波兰移民区、贫民聚居区、上流阶级邻里等作为单个小社区,进行深入调查和分析研究。其间也参照了里斯拍摄的纽约贫民窟以及海因拍摄的有关移民劳工的图像档案,但最终却没有借助摄影形成一个有关这个城市各个社区研究的的完整的图像规模和视觉描述。
几乎是同时,在中国也有一批社会学家出版了他们的重要著作。尽管我们看到像费孝通先生的《中国农民生活》(江村经济)这样的社会学著作中也附有部分图片,但相对于整个研究范围和对象来说,这些图片不仅无法构成一个系统化的视觉整体,而且图像的表现力也不令人满意。他的另外一些重要著作如《乡土中国》和《禄村农田》;与他同时代的其它社会学家如张子毅先生的《易村手工业》和《洱村小农经济》;史国衡先生的《个旧矿工》和《昆厂劳工》;当代一些大家所熟悉的社会学家如潘绥铭先生研究20世纪90年代中国东南地区色情产业状况的《存在与荒谬》;李银河女士研究中国女性情感生活形态及同性恋者生存状态的著作《中国女性的感情与性》、《同性恋亚文化》和《虐恋亚文化》等等著作,基本上还是依赖于文字的叙述分析以及大量的数字统计来传达相关的信息。问题在于,这些信息要依赖于读者的经验性想象活动才可能获得。由于个体经验的差异及影响,最终获得的信息已不再是作者所要传达的所有信息。相比较而言,如果这些报告附有一个与文字平行存在的完整的图像叙事体系,这种信息传达就会准确、丰富得多。而且从摄影的发展和记录传播的功能角度来说,一种已经非常普及的视觉记录形式,理应被广泛地应用于这种调查活动,并作为整个社会学研究表述的一部分出现在最终的文本当中。
这就是赋予照片以社会学功能的价值和意义之所在。 从目前中国一些摄影家的工作方向来看,以一个社会工作者的身份而不是摄影家的身份,从社会学的角度来从事摄影工作已经成为一种新的趋势。人们已经不再过多地迷恋于那种徒慕虚名式的得奖,也不再满足于那种按下快门就走的浮躁浅薄的工作方式,而是审慎地选择一个村庄、一条街道、一条河流、一类流动人群、或者一种人文景观作为观照对象,然后沉下心来,积数年之工夫,一方面大量采集图像资料,一方面通过长时间的调查访谈,取得大量一手的文献资料,然后集结成一个内容丰厚的有一定学术纵深和持久价值的文本。这和以往摄影家们出版的那种单纯的摄影图册有很大的不同。吴正中完成的“老青岛”、侯登科的《麦客》、张新民的《流坑》、赵铁林的《聚焦生存》、李玉祥的《老房子》、黑明的《走过青春》,等等,都已经明确地显现出一种迥异于以往的摄影视角。
苏州路,1998年
苏州路,2003年
苏州路,2006年
这并不是说只有使图像具有这种社会学功能时才是最好的。图像的这种社会学功能只是照片所应具功能的一种。它与图像的新闻传播功能、个人表现的功能、语言建构的功能以及观念传达的功能具有同样的价值,无以分高下。 之所以这样强调图像的社会学功能,是因为我们以往的摄影工作很少以一种特别沉潜的心境来注意到图像还会有这样一种复杂丰富的功能和表现,同时也对这种具有社会学价值及功能的图像性质和操作方式缺乏了解。我们总是过于笼统地将摄影看成是一种没有层次分别的视觉形式,甚至仅仅是将摄影看成是一门“艺术”,很少从功能的角度将图像制造分别开来,以致于不能正确地看待那些自己所不熟悉的摄影形态,也不能明白自己的摄影活动处在一种什么样的位置上,无法对自己拍摄的图片给出一个准确的价值判断,更不清楚自身以后的摄影发展方向。
02
服从于社会学的学术体系,运用社会学方法
那么,如何才能赋予图像以社会学功能和价值呢?
从整体策略和操作的层面来说,首要一点是转换摄影的观念和视角,服从于整个社会学研究的视角和系统方法,来观看和对待研究对象,以使摄影脱离惯性的运作体系。
观念的转变总是第一重要的。我们所熟悉的新闻摄影是对当下时空不断发生着的一些事件与人物活动的影像捕捉。它总是处于一种流动的运作状态之中,对于整个社会与文化生态而言,它更关注的是这个世界当下的表面现象。而我们一向迷恋的所谓艺术摄影则过多地迷恋于摄影家个人世界的视觉表达。纯摄影则只关心呈现某一具体事物的表面状态并同时炫耀材料的视觉张力(如韦斯顿),或者展示事物在某一瞬间中的完美组合形态(如布列松)。显然,这些摄影形态的目的与社会学的目的完全不同,其操作方式和图像属性也就无法满足社会学意义上的社区研究或其它研究方向。最明显的一点就是,一些从摄影专业的角度来看完全没有价值的图像,却有可能在一份社会学报告中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相反,一些摄影佳作,一些充分显现了摄影家个人才华与情绪的图像却没有任何的社会学意义。可见,这是两个极为不同的价值体系。要使照片具有这种社会学功能,就必须了解社会学研究的价值判断标准及运作方法,并按这种标准和方法来处理所有的图像。
社会学涉及到一个广阔的研究领域,每一个分支学科和研究方向都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诸如社会组织、人口流动、社会制度、家庭研究、婚姻问题、社会保障与救济、女权运动、社区结构与权力,等等。这和一般的新闻摄影、艺术类摄影、专题性的社会纪实摄影所面对的对象是不同的。 即以吴正中拍摄的“老青岛”这样的倾向于社区研究的影像采集而论,社区乃是一个在一定的地理空间区域内,有一定的人口、一定的社会组织形式、一定的文化传统和人文环境的社会群体。像青岛老城区这样一个完整的社区有其相对独立的构成形式,有其发展历史和文化传承,有其共同的意识、权力形态和复杂的利益关系。与变幻莫测的新闻事件相比,它更像是一个自足自在的相对稳固的富有广阔深度的复杂系统。与表现性的或者是纯粹摄影所面对的对象相比,它不再关心摄影家个体的差异,也不再关心摄影自身的问题,它的规模和复杂性,决定了与社区研究相关的摄影活动必须摆脱常规的摄影法则,而大量采用社会学的研究方法。
这些方法主要包括实地的社会调查,个案研究和文献研究,等等。实地的调查,特别是抽样调查和访谈是我们所熟悉的方法。吴正中所拍摄的“老青岛”这一特定社区内的所有重要的街道、院落、居民生活状态的照片及访问所获得的第一手资料,都是通过这一方法来实现的。张新民数次赴流坑村采访,侯登科随麦客在西北各省四处游走,也都主要采用这一方法。而吴正中在整个有关青岛老城区的摄影记录中所做的《波螺油子路》专题和《崂山大院》专题,赵铁林在整个有关海口一带妓女生活的摄影记录中所作的《阿V姑娘的日子》等小的图片专题,则混和采用了个案研究的方式,即通过对一少部分社会单位如个人、团体、局部社区(如一条街道、一座院落)作深入的调查和拍摄,通过长时间的观察、访谈,了解其详细状况和发展过程,弄清个人行为与整个社会环境的相互关系,从而获得整体研究和图像表达的细节与深度。
吴正中《崂山大院》系列
在摄影活动中引入文献研究的方法,是用于社会学目的的摄影一个突出的特点,也是目前中国摄影家最缺乏的一种图像意识。所谓的文献研究,即通过对大量第二手历史文献资料的搜寻甄别、考据整理和比较分析,来获得当下无法得到的重要历史信息。这些信息是整个社会变化的动态过程及其结果,它可以详尽地显示出社会变迁各个阶段的丰富内容。对于具有社区研究性质的摄影活动来说,这种有关社会变迁的文献信息尤为重要。对一个关注图像的社会学价值和功能的摄影家来说,这意味着除了拍摄整个研究范畴中所涉及到的当下的相关图像外,他还要尽可能地寻找采集与研究对象相关的一切历史图像资料,并把它有机地纳入整个视觉研究的图像系统之中。
台湾摄影家张照堂先生近年来编辑的《淡水河》,即是完全使用搜集整理出来的文献资料和他人记录的图像资源构成的一部以一条河流的人文生态为研究与表达对象的具有社会学价值的著作。这些历史图像往往来源复杂,语言简单雷同,而且质量较差。对于一个过分迷恋自我和摄影本身的人来说,这些图像往往会处于他的视野之外。但对于一个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待图像价值的摄影家来说,这些图像所承载的历史信息是极为珍贵和无法替代的,它甚至要比摄影家自己正在拍摄的这些照片更为重要。因此,他必须按照整个社会学研究体系的需要来选择和使用这些图像,而不能按照自己的好恶和摄影本身的专业要求来取舍这些图像。
张照堂作品
03
规模、系统性与完整性
除此之外, 具有社会学功能的摄影还须达到一种规模化的运作,依据整个研究话题的内在逻辑结构,以最终形成完整而系统的图像表达。这种规模,这种系统性和完整性是一般意义上的纪实摄影和图片专题摄影所无法相比的。当我们拍摄一个图片专题时,我们会大致设计一个叙事结构,依次将图片串连起来,以展示摄影家所看到事物。这个结构秩序基本上是在报道摄影内部形成的一种读解习惯,比如以哪张照片开头,以哪张结束,哪张应是特写,哪张应是全景,图片之间有一种视觉语言上的内在联系和表述节奏。由于摄影家个人悟性的不同和处理题材方式的差异,这种图像之间的关系具有相当大的随机性。由于这种专题摄影自成一个叙事结构,所以规模也往往不能充分展开。
相比之下,由于整个社会学研究的体系化,它要求随之而来的影像叙事也要构成一个具有相应规模的图像体系。 具有社会学功能的图像只与它所依附的社会学研究内容形成紧密的对应关系,而这些图像本身之间并不构成像在摄影内部那样一种紧密的视觉连续关系。它们或成为一个个单元,或者相互之间仅有一种松散的视觉意义上的关联。只有将整个社会学报告和这些照片统一在一起看待时,我们才会发现它们那种内在的整体的紧密性。从这一点上说,具有社会学功能的图像看上去有点儿像在为一份复杂的研究报告所作的大规模的摄影插图。
以吴正中的拍摄的“老青岛”为例,当他拍摄“胶东路3号”、“长清路2号”、“章邱路一院门”、“从胶东路36号楼上望去一景”时,这些照片基本上构成一种类型化的图像,之间并没有一种紧密的关联,而且仅有一二十幅的规模时也显现不出多大价值。但是,当它们被涵盖于整个“老青岛”这一大的社区研究的观照之下时,当吴正中踏遍每一条老青岛的街道,造访所有有代表性的院落以及那些居住于此地的人们时,当这些照片记录下所有与老青岛城区有关的事物并达到相当的数量规模时,这些图像之间便不再是一种松散的关系,而是获得了一种有机的关联和整体的一致性,其作为整个“老青岛”城区的视觉证言的社会学价值便开始显现出来。相比较而言,吴正中以图片故事的专题摄影形式先行发表的“波螺油子路”、“崂山大院”、“小本买卖”等,则要较多地考虑一些有关专题摄影本身的结构规则、图像的视觉强度及图像间的内在关联,以在这些较小规模的图片专题当中尽可能集中地传达更多信息。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那种具有社会学功能的图像采集与我们已熟悉的那种专题摄影的微妙差别。
吴正中《波螺油子路》系列
04
弱化对图像语言的迷恋,强化图像的叙事性
从图像本身的角度来说,用作社会学研究目的的图像还必须具有其它一些重要特征。首要一点是要弱化对摄影语言本身的过分关注,以使图像服务于整体记录和丰富叙事的目的。
弱化对摄影语言的过分关注,即是把摄影仅当作一个具有表述功能的必要工具来看待和使用。 显而易见,有关一个社区研究的大规模图像采集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展示摄影本身,而是为了以图像的方式显现社会学者所关注和研究的话题及对象。因此,在整个话题的研究过程中,一方面,图像传达要与文字表述紧密结合,有时甚至要屈居插图的地位。另一方面,图像的视觉独立性不再具有意义,在任何一份社会学报告里,图像都不是为了视觉观赏的需要,而是为了叙事的动机。
问题是,在许多摄影家的认识中,摄影始终是一种“以视觉语言为其存在形态的艺术”,所以,一张照片的内涵只能通过照片本身来显现时才是一张好的照片。如果一张照片沦落到了通过文字来阐释其内涵的地步,这张照片本身就是失败的。 一个摄影家只能通过他所创造的图像来表达他所要表达的东西,而通过文字来言说那是文学家们做的事——这种误解一直左右和束缚着相当多的摄影家。
其实,当我们转换一种角度,不再将照片作为一种独立自足的视觉图像来看待,而是作为一种叙事语言来向受众描述他所面对的一种具体对象时,纯粹的视觉语言的有限性便会显露出来。当你面对一个动态对象,比如像侯登科拍麦客那样面对一个流动的人群,并企图通过你拍下的一幅幅静态图像来描述这个人群的生命状态时,图像便会显得十分单薄和平面化。充其量它只能是有关这个群体的一种象征性的图像表达。对于像中国前卫艺术家、陕北知青、西海固回民、麦客、海南妓女这样的群体,对于经历了苍桑变迁的老青岛、流坑这样的社区,单纯通过一些视觉图像总是无法表达它们的无限丰富性和复杂性。即使表现力再强、数量再大的摄影静照,也不及一段模糊不清的纪录影片或者是录像资料的表达来得充分。因为动态对象的存在形式中有一个照片所无法完整显示的“时间”和“过程”性因素。当这个动态对象的规模较大而其延展过程较长时——比如关于一个村庄的历史与现状,一个城市社区的变迁,一种人群的流动与生存状况,一条河流的人文生态,等等,时间的延宕及空间的整体性便会显得格外重要。尽管人们会不得已地通过图片故事这种连续影像的叙事方式来表达这种时空绵延的整体性,但是,这些图片仍然要依赖于明确的说明文字才能相对准确地阐释这一过程。而真正将时间过程性因素纳入表达本身的只能是电影或者电视这样的语言形态而不是摄影静照。
这就是说,图像不是万能的,它不能做所有的事。图像作为事物的表象,它在显现出事物部分内涵的同时,却挡住和掩盖了更多的东西。因此,要在社区研究过程中通过图片来完整地展示这一对象复杂丰富的“过程性”内容,就必须采集到大量的记录整个社区变迁过程每个重要阶段的图片,这些图片将构成一个相对完整的视觉连续的过程。另外则需要与整个研究报告相配合,以大量的尽可能详备的可以超越时空的文字叙述、数字统计和逻辑分析,来展示图像背后的和图像本身所无法表达的过程性内容。摄影家不再关心和展示摄影的自律性,不再迷恋视觉语言的精纯和地道。他只是在用图像来叙事。只有这种意义上的图像才可能有效地嵌入到社会学研究的整个过程当中。
中山路,1998年
观象二路,1996年
吴正中的“老青岛”,张新民的“流坑”以及其它一些引入大量文字叙事的摄影家出版的图书,已经开始从已往那种过分迷恋摄影的视觉语言状态、过分关注影像制造的状态中脱离出来,其操作方式和心境已经很接近社会学家做田野调查的心境和操作方式。
比如,张新民的《流坑》是有关一个乡村社区的历史变迁与现状的调查研究;李玉祥的《老房子》是对一种历史人文景观的大规模描述;吴正中的《老青岛》完整展现了一个城市社区的整体状态与历史变迁;肖全的《我们这一代》、赵铁林的《聚焦生存》、黑明的《走过青春》、侯登科的《麦客》)等等,则侧重描述了一种人群的流动、聚集及其生存状况。这些融入大量文字叙事的画册,已经大大弱化了摄影语言的纯视觉特性,不再炫耀图像的视觉意义上的独立价值,显现了具有社会学功能的影像的一些基本特征。
05
抑制摄影家的个性表现
使图像具有朴素明确的素质,努力排斥图像的象征性和多义性,以更好地满足社会学研究的需要,还必须消解摄影家的“艺术家”情结,最大限度地在摄影中抑制个人化的表现欲望。
对于一个中国摄影家来说,认同并做到这一点并非易事。因为长期以来,中国摄影家有关艺术的理解,就是它可以表达“艺术家个人的精神世界”。“个性”已经成为一个倾向鲜明的词语,它成为所有艺术家追求和表达的东西,甚至已经成为了一种社会时尚和人生价值的指标。黛安·阿勃丝、威廉·克莱因、彼得·威金、强·索德克……这些摄影艺术家们营造的极富个人色彩的图像曾经深刻地打动并影响过我们。
问题在于, 社会学研究是一种人文科学而不是艺术。它有自己相对完整谨严的学术体系和运作规范。这就意味着社会学意义上的摄影活动是在为一种学科研究提供一个完整的图像叙事系统,而不再是什么“艺术创作”。尽管那些表现了艺术家个人情怀的图像充满了感人的个性魅力,尽管这种意义上的摄影会在艺术史上占有独特的位置,但是,这种表现主义式的摄影姿态却不适用于社会学研究这样的领域。因为,艺术摄影乃是一种具有强烈情绪化和选择性的“个人化的观看”,而用于社会学目的的摄影则是一种力求完整显现对象世界本身状态的客观化描述。在表现性的艺术摄影中极具感召力的艺术个性,在这种社会学目的摄影活动中却会成为一种尘埃和干扰的力量,它蒙蔽在对象世界之上,甚至会扭曲对象存在的真实状态。个人表现欲望所显现出来的强烈的内在冲动,是发生在自我中心主义基础上的,它是利己的而非利他性的。因此,个人表现欲所具有的强烈的选择性和排它性,决定了它无法遵循社会学研究的基本体系和运作法则,无法平静地通过摄影完整地观照和再现他所面对的对象世界,甚至会严重削弱社会学研究所要表达信息的客观性和可靠性。因此,有效地在图像采集过程中抑制这种个人表现的冲动,是使图像具有社会学功能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步骤。
禹城路,1997年
禹城路,1998年
海泊路63号广兴里,1996年
这就是说,当我们基于社会学的研究,面对一个更为重要的话题进行影像描述时,任何对于个体存在的执迷都会落入一种较为低下的境界之中。因此,作为一个摄影家,从对摄影本身和个人内在世界的迷恋,转而关注于个体之外的一种存在,并为这种存在努力工作,这是在走向一种更为广大和深邃的境界。 个性化的、艺术的表达固然会有它的魅力,但是关注于一个群体的生命活动、关注一个种族的命运,关注于他者的生存状况,并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影响那些可以改善这些状态的力量,其价值要广大重要的多。我们有理由期望看到一些头脑更冷静、心胸更开阔、有相当深厚的知识准备、更注重图像的社会学功能和学理严谨性的摄影家,他们不仅是图像的制造者,同时也是图像的采集者和一种社会存在的研究专家。他们将个人得失置于他所关注的对象表达之外,不再迷恋于自己出来说话,而是更注重让事物自己出来表达他们自身,他只是一个为这种表达提供机会的社会工作者。他们不再用一种艺术家的心情看待世界,他们更多地是用一种学者的眼光来看待他所面对的那些事物。他也不再心情浮躁地飘来飘去,他只是平静地面对一个村庄,一座小镇,一条街道,一条河流,一个民族,或者是一种人群,然后积若干年之努力,运用一套行之有效的社会学方法,深入而完整地呈现这一对象,并在这一工作中稳住自己的生活,寻找出其中富有普遍价值的内涵。我想,这种意义上的图像将具有更为恒久的价值和独特魅力,甚至会远远超过那些过分摄影化和个人化的影像。我们在吴正中、张新民、侯登科、王征、黑明等等这样一些摄影家的工作中已经看到了这一点,同时我们也期望看到更多的摄影家从事这样的具有建设性的工作,以真正使我们的摄影呈现出一种多元并存和稳步发展的局面。
原文刊载《中国摄影》杂志2000年第11期
现收录于《他的城:1978—2024年的青岛》
刘树勇(老树画画), 山东临朐人。1983年南开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毕业,执教于中央财经大学至今。现为该校文化与传媒学院艺术系教授。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致力于视觉语言与叙事方式的比较研究。90年代中期以后,转而关注当代中国摄影发展及传播过程中存在的相关问题。目前,主要从事视觉媒介的传播研究与具体实践。
往期分享:
刘树勇(老树画画):重要的是找到自己的声音
刘树勇(老树画画):我不是怀旧,我只是要记得
吴正中《他的城:1978—2024年的青岛》
1300余张照片
纪实影社画廊
▼
纪实影社 向优秀的摄影师致敬
纪实影社画廊 第一期
纪实影社画廊 第二期
纪实影社画廊 第三期
纪实影社画廊 第四期
纪实影社画廊 第五期
纪实影社画廊 第六期
纪实影社画廊 第七期
纪实影社画廊 第八期 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责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