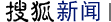尖锐的军事、意识形态两极对垒局面结束之后,不同文明之间如何防止冲突、和睦相处的问题,开始进入各国政治家和国际政治研究者的视野。
随着经济全球化步伐的加快,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日趋活跃。信息传播技术日新月异,各种文明走向世界,相互交流、相互借鉴的途径日益广阔。
文化因素在新世纪发挥的作用愈益重要,文化实力在综合国力中的重要性增强,文化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加大。然而,国际思想文化领域的斗争依然深刻复杂,某些强势文明凭借政治、经济,乃至军事手段,运用“话语霸权”,肆意侵害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文化权益的情况时有发生。与此同时,人类对宏观和微观物质无尽的探求,使科技革命加速推进,一些新的技术手段如使用不当,可能为潜在的文明冲突带来更为严重的后果。
因此,不同文明之间相互借鉴,求同存异,尊重世界多样性,共同促进人类文明繁荣进步的要求,就显得尤为迫切。
一
世界本来就是多样的,不同的文明本来就是平等的,这是文明对话的基础。
文明是全人类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当今世界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存在着2500多个民族。在漫漫历史长河中,不同的自然环境、不同的民族国家,形成了人类多姿多彩的文明形态,而文化则是各种文明的具体表现。文明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这种多样性将长期存在。
“物相杂,故曰文。”不同的文化和文明存在差异,而承载它们的各自经济基础也有一定差别,这些差异、差别不仅不是文明交流融合的障碍,反而是世界文明发展的活力所在。
翻开人类文明的历史,我们看到,各种文明都有其自身发生和发展的演变过程,都有其自身的特点和优缺点,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起着不同的历史作用。历史上的一切文明成就都是对全人类文明的宝贵贡献,都应得到充分承认和尊重。我们认为,不同文明有历史长短之分,并无高下优劣之别。
当欧洲人最初到达非洲时,他们发现非洲根本没有书面记载的历史,于是,有人认为非洲是缺少文明史的大陆。但当他们真正深入非洲民间,发现普通非洲老人坐下来谈起本部落的历史,上下千年尽在腹中时,才意识到自己的看法存在着极大的偏见。随着近代考古发现,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非洲是人类文明的主要发祥地之一。
人类应该感谢多种文明的存在,正因为世界上存在着多种多样的文明,人类社会才得以不断发展,世界才呈现丰富多彩。
但是,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带来了文化产业发展的不对称日益增大,欠发达国家的文化产品在全球文化传播过程中被忽视甚至逐渐被边缘化,而以强势经济手段为传播依托的西方文化形成文化霸权。文化交流的严重失衡,不断侵蚀着世界文化的多样性。
在当今全球信息流动中,90%以上的新闻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控制的;美国的电影、电视作品生产量仅占世界总量的6.7%,但电影流通量却占了世界市场的50%以上,电视作品的比重更是超过了70%。
语言是文化的重要载体,但世界上的一些语言正在逐渐消失。按目前的消失速度,在未来100年间,世界上现存的5000多种语言将会消失一半,另有多种语言也面临严重威胁。
如何让经济社会发展处于弱势的文明群体,获得平等交流、各美其美的权利,成为全人类共同的责任。
二
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宗教之间的碰撞、摩擦乃至对立、冲突,在人类历史上并不鲜见;然而,和谐共处、相互影响、相互渗透乃至交融互变,才是世界文明发展的常态现象和主流。正是这交流互鉴的常态,人类取得了从茹毛饮血、刀耕火种到解开生命密码、探索宇宙奥秘的巨大进步。
文明的发展与繁荣离不开文明间的交流互鉴。从本质上讲,一种文化在任何时候都是一个动态的、开放的、不断变化着的系统,它的发展壮大永远离不开与其他文化的交流、沟通与传播。印度人发明的数字,经过阿拉伯人的改造和传播,最终成为全人类共同的数学思维基础。而中国的四大发明,极大地促进了人类文明的传播与交流。
现代西方文明也曾广泛汲取世界文明的成果。例如,17、18世纪,当外国传教士把中国的文化典籍翻译成西文传到欧洲时,曾引起一批著名学者和启蒙思想家的浓厚兴趣。笛卡尔、莱布尼兹、孟德斯鸠、伏尔泰、歌德、康德等,都受到过中国文化的影响。
地球是圆的,任何一点都可能成为它的中心;文明是有自尊的,任何一种文明的主体都希望其成为“世界的中心”。但是,事实证明,任何一种单一文明都不可能成为真正的“普世文明”。不承认、不尊重世界文明的多样性,企图建立一种文明的一统天下,最终注定要四处碰壁。任何企图侵蚀甚至用强力铲除其他民族国家的文化和文明的努力,必然会使自己的文化和文明发生异化,并逐步走向衰落甚至毁灭。历史上不少霸气十足的国度,煊赫于一时,最终都没有逃脱衰败甚至毁灭的命运。
文明是相对野蛮而言的,因此,不同文明之间必然又有其同一性。文明对全人类的“普适性”是在相互交流、相互促进中形成的共同价值观,这为文明的对话与文化的交流创造了前提。例如,各种文明的深层结构中都包含着对人的热爱、关怀和宽容。西方文明中的“博爱”、中华文明中的“泛爱众”、佛教文明中的“慈悲为怀”、伊斯兰教义中说的:“你觉得什么是痛苦,就该想到对所有人都是痛苦。”各种文明中的这些核心内容相通,可以携手共进,为文明的对话铺就了一条便捷之路。
和而不同、有容乃大的和合文化,是中华民族长期积累形成的关于文明对话、交流互鉴、共同繁荣的重要智慧。发源于北非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文明、发源于两河流域的巴比伦文明、发源于恒河—印度河流域的古印度文明、发源于黄河—长江流域的中华文明、发源于地中海北岸的古希腊—罗马文明等,都是举世公认最早出现的文明。但由于各种原因,这些古老文明有的衰落了,有的消亡了,有的融入了其他文明,而中华文明却历经沧桑完整地延存了下来,并依然充满生机,继续繁荣兴盛,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便是中华文明一直保持着开放和包容的心态,不妄自尊大,不排斥外来文化,而是不断吸收外来文化以丰富自己。玄奘取经、郑和下西洋,早已成为人类文明交流史上的佳话。如今,印度的佛教文化、柬埔寨的吴哥文化,等等,常常从中国古代的典籍中去追寻其失落的辉煌。
三
当代政治和经济发展为文明对话与文化交流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冷战结束后,阻碍文明和文化交流的藩篱逐步拆除,文明和文化交流的障碍日趋消解。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的推进,为文化多样性的发展提供了更为有利的条件。
然而,不同文明之间的碰撞、摩擦乃至对立、冲突依然存在。除局部地区不同文明、不同种族的仇恨由于历史积淀,一时难以消弭之外,一些国家打着所谓“民主”、“自由”、“人权”、“法治”、“良政”的旗号,贬低、排斥别的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和文明,大肆推销其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社会制度,加紧对一些国家进行文化渗透,侵蚀别国民族文化根基,加剧了一些地区的民族冲突和宗教矛盾,特别是使发展中国家的政治文化、信息安全面临严峻挑战。
西方文明在消费主义的旗帜下向全球渗透,严重挤压其他文明的生存空间,这势必引起其他文明群体的不满、恐惧,乃至愤怒;而近代以来形成的“西方中心主义”的傲慢与偏见,又推波助澜,大肆渲染这种矛盾、对立。“9·11”事件之后,将恐怖主义与特定民族、宗教挂钩的极端做法,更是将西方与非西方的对立推向高潮,于是,“文明冲突论”一度甚嚣尘上。
世界各国不带偏见的政治家都认为,反人类、反文明的恐怖主义从来与任何文明、宗教无关;要消除“文明冲突论”引发的恐慌,唯一的办法只有开展文明对话,加强沟通,消除异质文明之间的误解与曲解。
中国国家领导人多次强调,中国主张维护世界文明多样性,促进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对话、互鉴;各种文明应该和平共处、取长补短、共同发展。
中国一贯反对在文明对话、文化交流中运用“话语霸权”,始终认为,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是一个国家文化、文明的核心和本质所在,尊重和维护文化和文明的多样性,必须尊重和维护基本制度与发展道路的多样性,反对政治和经济上的单边主义。
中国既积极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华文明,也努力吸收、借鉴其他文明的有益成果。近年来,中国与一些国家合作,举办了各种形式的“文化行”、“文化节”、“文化周”和“文化年”活动,促进了中国与有关国家人民之间的深层次了解,为不同文明和文化的对话开辟了新途径。
法国人戴高乐说,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比地球和月亮的距离还大;但另一个法国人雨果说,比天空更广阔的是人的心灵。前者说明人类必须加强交流,后者则说明人类可以进行交流。
我们相信,只要各民族国家人民展开比天空更广阔的心灵,以更大的真诚与热情,拥抱、理解不同的文明和文化,世界必将变得更加绚丽多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