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坐落在皇村的普希金雕像
也许是基于几年前的那次出访得出的印象,我对俄罗斯文化的那种无处不在的恢宏与高雅,充满了崇敬之情。为此,我不仅在那篇《俄罗斯文化之旅》的长文中发表了自己的观感,而且还投入了很大的精力,和另一位翻译家重译了普希金的部分抒情短诗以及他的长篇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
我是将普希金作为俄罗斯文化的一种象征来加以研究的。他的诗,有如海波的喋喋一样柔和优美、勇士剑击一样的坚固有力,具备了一种非言语所能形容的迷人的美和优雅。所以,别林斯基说,阅读普希金的作品,是培育人的最好的方法,对于青年男女有特别的益处。他认为,在教育青年人、培育青年人的感情方面,没有一个俄国诗人能够比过普希金。普希金的诗没有奇幻的、空想的、虚伪的、怪诞的理想的东西,它整个浸透着现实。
我在研究中发现,俄国文学史上有一个奇特的现象,即在12世纪出现了杰出的史诗《伊戈尔远征记》之后,文坛差不多沉寂了500年,直至18世纪末叶才又重现曙光。到了19世纪,以普希金为前导,名家辈出,一跃而为世界文学中的大国之一。此后不到半个多世纪,在19世纪80年代,俄罗斯文学竟那样地征服了欧美各国的读者,以致欧美的评论界惊呼俄国文学的“入侵”。不少欧美名作家都承认自己师承普希金、屠格涅夫、列夫·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更多的作家对俄国文学感到亲切,并为之赞叹不已。
在圣彼得堡,我曾询问过一位俄罗斯作家:苏联解体之后,面对西方的大众文化、尤其是美国文化的冲击,俄罗斯文化怎么保持它民族的传统的特性?他不以为然地笑着说:在生活层面上确有影响,现在俄罗斯人喝可乐,但再过些时候,他们还会喝克瓦斯(俄罗斯本土产的碳酸饮料)。正因为俄罗斯文化比美国文化要久远得多,这里指的是文化的渊源与素养,俄罗斯人从小就读经典作品,读普希金,这是中学大纲里要求的,这些要求的东西要远远超过那种所谓的大众文化的品位。
翌日,我们即驱车去了离圣彼得堡仅30公里的皇村。位于芬兰湾南岸森林中的皇村,就是普希金诗的萌发地。我曾经在那里留连忘返,希望能获得一点诗的灵性。我确信,这里的树林、林中的草地以及草地上的金黄的落叶,给了普希金无尽的诗的灵感。这里的一切,包括树皮的颜色、树干的强壮和那使雄伟的风景倍增起来的如镜的湖面在内,都带着和谐的力量打动了少年普希金的诗心,激发起他的才情———即他自己所说的“最美好的、宜于接受印象和把它们传达给周围人的情绪”。也正是有了这样一种“激励的情绪”,才有了普希金的《皇村忆旧述怀》、《皇村》、《皇村雕像》、《“皇村学校愈是频繁地……”》等一批传世之作的出现。
普希金曾在他的《10月19日》这首诗中写道:“无论命运会把我们抛向何方/无论幸福把我们向何处指引/我们———还是我们:/整个世界都是异乡/对我们来说/祖国———只有皇村。”显然,诗人把他永无穷尽的文化乡愁和永无止境的家国之思糅在了一起,将“祖国/皇村”的概念提到了俄罗斯文化的层面。事实上,皇村也是普希金之后又一批诗人的发迹地,此中有莱蒙托夫、涅克拉索夫和阿赫玛托娃,可以说,皇村也是这些诗人学习、生活、焕发诗情的灵性之地。这些诗人们几乎都将皇村视为创作上潜在的动力,将皇村看作思维的一种形式和创作的一种兴趣,于是,皇村因此而成为俄罗斯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记得在那次踏访中,我对皇村那座金碧辉煌的叶卡婕琳娜宫和极尽奢华的琥珀厅,作过哲人般的审视:当年这里出将入相的显赫、森严与林间小路上诗人的独自行吟反差何其之大,但各自留给历史的又是什么呢?待我穿过一片橡树林,普希金黝黑的雕像赫然出现在我面前时,我似乎找到了答案———我记起了15岁的普希金写的《皇村忆旧述怀》中末尾的诗句:
叶卡婕琳娜的好孙子啊!我为何不像你一样满怀激情?
我们当代天才的诗人、斯拉夫军旅歌手啊!
你现在就让诗神阿波罗
给我胸膛注入惊人的才能吧!
有你的激励和鼓舞,
我也会用竖琴,
让铮铮弹响的天上乐曲,
在黑暗的人间大展风韵……
诚如19世纪的俄罗斯诗人丘特切夫所言:“用理性不能了解俄罗斯,用一般的标准无法衡量它,在它那里存在着特殊的东西。”我以为,这个特殊的东西,就是“俄罗斯精神”和蕴含着这种精神的俄罗斯文化。要了解俄罗斯,就不能不走进博大精深的俄罗斯文化。我记得还有一位后来做了总统的作家说过这样的话:文化,应该包括人们全部的日常生活,包括人们的教养和素质,因此,崇高的信念和理想都与文化有关,一个国家的公民在文化教养上的衰退与道德上的沦丧,比大规模的经济衰退更为可怕。诚哉斯言! | |
|



|
|
|
|


| 今日运程如何?财运、事业运、桃花运,给你详细道来!!! |
 |
|
|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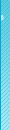 |
 |
月亮之上 |
 |
 |
 |
|
 |
秋天不回来 |
 |
 |
 |
|
 |
求佛 |
 |
 |
 |
|
 |
千里之外 |
 |
 |
 |
|
 |
香水有毒 |
 |
 |
 |
|
 |
吉祥三宝 |
 |
 |
 |
|
 |
天竺少女 |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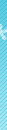 |
|

|
|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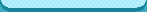 |
 |
一个人哭 |
 |
|
 |
退后 |
 |
|
 |
断了的弦 |
 |
|
 |
还是朋友 |
 |
|
 |
水晶蜻蜓 |
 |
|
 |
唱给你的歌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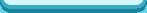 |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