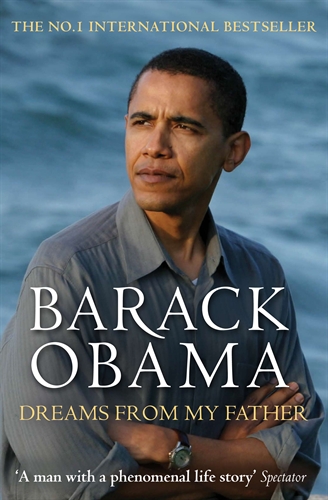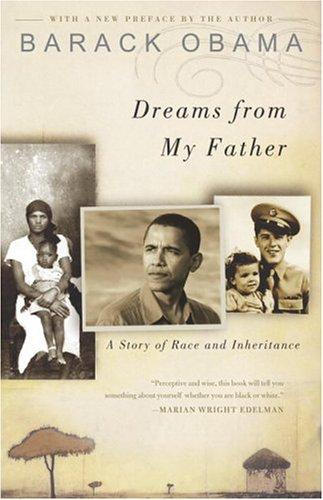新华网北京7月17日电(杨潇)美国总统奥巴马传奇身世一直是美国人津津乐道的话题。近日,英国资深专栏作家詹尼特·斯科特经过两年半调查采访,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奥巴马母亲的海外往事》一文,讲述了奥巴马和母亲在印度尼西亚的经历,凸显了母亲在奥巴马人生中的重要作用,还原了一个真实感人的母亲形象。
为保持文章的原汁原味,新华网国际频道翻译沿用了第一人称形式编译了全文。译文分三部分连载,敬请关注。今天是第二部分。
奥巴马母亲的海外往事(之一)
安·邓亨1967年来到印尼的时候,这里还是一片令人震惊的状态,而她却要在这里度过占了她成年生活大部分的时间的三段居住期的第一个阶段。那次阴谋和反阴谋的细节今天仍有争论,接下来的大屠杀的细节也不得而知。但可以明确的一点是,即便是友邻,也难免互相戕害。《现代印度尼西亚史》的作者阿德里安·威克斯认为,那时候军队挨家挨户盘查每个村庄,有嫌疑的人,强奸妇女,甚至迫害儿童。“证明你自己不是共产党人的最好方法就是加入这场杀戮,”威克斯写道。比尔·科勒是安·邓亨的朋友,他1968年来到印度尼西亚,在农村做了15年的社会经济调查。他告诉我说,当时有人告诉住在咸水河道旁的研究者们,他们不能吃河里的鱼,因为水质已经被腐烂的尸体污染了。还有很多印尼人选择沉默,从来不说那时候到底发生了什么。
安·邓亨·索托罗和她的儿子第一次见到的雅加达,是一片村庄聚集而成的地区,房屋低矮、杂乱无章,和密林、稻田还有泥沼交织着。破旧的都市村庄(印尼语“堪彭村”)中,狭窄的街道通向密集的瓦房。破旧的居民区分布在运河两岸,人们在这条河里洗澡、洗衣服、倒脏水。从十一月到次年三月是漫长的雨季,运河河水泛滥,纸板搭建的棚屋被淹没,洪水侵袭着城市的大片地区。居民们出门主要靠走路、骑自行车或者乘坐人力自行车(印尼语叫做“贝卡克”)。停电是家常便饭。能用的电话也很少,甚至据说街上的大部分轿车是为了给办公室之间送信的。“秘书们甚至要花上几个小时去一次次地拨电话号码才能打通电话,”1968年迁来印尼的美国人哈里玛·布鲁格对我说。当时西方人很少,黑人更少。西方女人更使人们好奇。“我还记得穿着短裙坐着"贝卡克"上街的时候,人们甚至轰动了。”布鲁格说。从美国寄来的信要好几个星期才能到达收信人手中。外国人遭受了各种肠胃不适的折磨,除蛔虫更是司空见惯的事情。
但是这座城市的另一面却富有魅力。奥巴马以及那些在雅加达度过童年时光的人们,一直对穆斯林召集信徒们集合的宣礼声念念不忘,那时候还没有广播。街边的小贩们喊着叫卖的调子,推着推车穿越棚户区。当时在古老的印地酒店的阳台上依然提供茶点。在午后的燥热中,天花板上的吊扇慵懒地打转,煤油灯在夜色笼罩下的窄巷子中闪烁着光芒。对于那些政府保安力量不感兴趣的人来说,生活简单而自在。对外国人来说,在1967年迁到印尼但对两年前的恐怖形势一无所知是完全有可能的。“我对整件事了解甚少,”布鲁格说。“那时候一切都结束了,我从来没有一点哪怕是最轻微的被威胁的感觉。”威克斯的书中写道,许多年之后,很多人会怀念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那一段时光,认为那是一段蜜月期。政府对媒体的管制有所放松,年轻人的文化开始兴起,文艺文化生活变得兴盛起来。后来有人说,那几年是印尼的布拉格之春。
安·邓亨来到印尼的时候,洛洛正在军中服役,薪水很低。后来她向一个同事抱怨说,她在印尼度过的第一个晚上,洛洛给她吃了白米饭和“丹登侧楞”(一种风干的野猪肉,印尼人在食物短缺的时候会在森林里猎取这种动物来填饱肚子)。不过后来洛洛服完了兵役,他的姐夫特里索罗动用了印尼国家石油公司副经理的关系,为他在加州联合石油公司驻雅加达分部谋得了一个职位。70年代初,洛洛和安·邓亨搬到了雅加达的中产阶级居住区马特拉曼的一个出租屋。这间屋子是一个“帕威林”,也就是一座大房子的附属建筑物,有三个卧室,一个厨房,一个浴室,一个书房和一个阳台。像其他有一定经济实力的印度尼西亚家庭一样,他们有人数可观的佣人们:两个女佣住在一间卧室里,两个男仆人一个厨师和一个童仆大多数时候睡在地上或者花园里。仆人的辛勤劳动使得安·邓亨免于做家务,轻松的程度甚至是在美国都不可能的。有人打扫房间,做饭,购买食品,照看她的孩子这样她就有时间能够从事自己的工作,追求自己的兴趣,甚至随心所欲地来去。同时这些仆人也让安·邓亨和洛洛有机会去培养自己的职业和社交圈子,而两人的圈子并没有太多交集。
到1968年1月的时候,安·邓亨已经作为美方主管在印尼-美国事务局工作了,这是一个两国合作的组织,由美国信息服务中心资助,下属于美国国际开发署。她管理一小组教授英语的印尼人,他们给印尼公务员和被美国国际开发署派到美国进行研究生学习的商人们上英语课。但是安·邓亨非常讨厌这份工作。“我在雅加达的美国大使馆度过了极其可怕的两年,”她曾在给友人的信中这样写道。奥巴马在回忆录中提到这一段工作时说:“印尼商人们对英语的精确细致性不感兴趣,还有几个人向她调情。”偶尔几次,她带着奥巴马去上班。印尼人乔瑟夫·西吉特当时在那里担任办公室经理,他告诉我说:“我们的工作人员有时候会嘲笑他,因为他的肤色看起来与其他人不同。”
是和他开玩笑,还是开他的玩笑?我问道。
“两个都有。”西吉特说,没有丝毫的尴尬。
两年后,也就是安·邓亨27岁的时候,她被雇佣去在印尼的一个私人非盈利的管理培训学校中成立商业沟通学系。这个学校叫作管理教育和发展研究院,是几年前一个希望帮助培养印尼社会精英的荷兰牧师建立的。她参与了培训教师、制定课程大纲和教授高层主管的工作。作为回报,她得到的不但是一张支票,还有这个项目的分红。她还成为了一名受欢迎的老师。安·邓亨的课堂“简直是从头到尾充满了欢笑,她有极好的幽默感,”70年代在研究院兼职授课的莱纳德·奇波这样说。有的笑料来自安·邓亨那还不太完整的印尼语知识。奇波说她经常提起的一个笑话是:她想告诉一个学生如果他学了英语,他就能“晋升”。这个短语在印尼语中应该是naik pangkat,但她说成了naik pantat。其实前者的意思是“提升地位”,而后者则是“抬起臀部”。
同一年的8月15号,在奥巴马的九岁生日和安·邓亨的母亲玛德琳·邓亨唯一一次来访印尼之后不久,安·邓亨在雅加达的圣卡罗斯医院生下了玛雅·卡珊德拉·所托罗。这是一所天主教医院,当时被西方人认为是雅加达最好的医院。哈里玛·布鲁格两年后也在这家医院生了孩子,她告诉我说,医生接生的时候甚至都没有听诊器、手套和医生制服。“孩子生下来的时候,那医生向我丈夫要了一条手帕,”布鲁格说,“然后她把手帕塞进我嘴里,没打麻药,给我封了11针。”安·邓亨给这个新生儿想了三个梵语名字,最后决定叫她玛雅·卡珊德拉。玛雅告诉我说,这个名字对于母亲很重要,她想要“美丽的名字”。安·邓亨在童年所讨厌的那个名字“斯坦利”根本不在考虑范围内。
在印度尼西亚,安·邓亨是一个引人注目的形象。“也许只看她的外表和举止就能感觉到这种吸引力,”安·邓亨在1971年雇佣的哈里玛·贝罗斯说。她打扮得很简单,几乎不化妆,留着长头发,在脑后用皮筋扎起来。从爪哇文化的角度来看,按照她的印尼同事费力那·普拉莫诺的说法,她“比一般的女人要强硬得多”。她有坚定的立场,而且从不为了取悦他人而妥协。
安·邓亨最好的朋友之一凯·伊克兰娜加拉用近乎宠溺的口气说:“她曾经快把我逼疯了。”安·邓亨对她说她要学着大胆、强硬一些,嘲笑她不高明的厨艺,让她和家里的仆人说清楚该怎么做,而不是让她们肆意妄为。“她对每个人都是这样,毫不犹豫地说出来他们哪里不好,”伊克兰娜加拉说。连她的家人也不能幸免;伊克兰娜加拉回忆说:“她十分讨厌传统印尼妻子的角色,她告诉玛雅不能如此懦弱。她不喜欢印尼女人消极不主动的形象,还会告诫我不能变成那样。”
伊克兰娜加拉是一位加州大学发展经济学家的女儿,这个人在50年代末印度尼西亚大学教书。她少年时住在雅加达,60年代去加州伯克利分校学习人类学和语言学,之后回到了雅加达,遇见了她后来的丈夫。她在管理学校兼职授课并撰写语言学博士论文的时候结识了安·邓亨。她们有很多相似之处:她们都有印尼血统的丈夫,都有人类学学位,她们的孩子在相同的月份出生,都有60年代局势塑造的观点和想法。伊克兰娜加拉对我说,她们对文化间的隔阂不像其他人那么敏感,也反对她们眼中前代人对于种族问题的虚伪的态度。“我们的观点完全一致,”她说,“石油公司或者使馆的职员当然属于一种和我们不同的文化,但是,我们觉得他们也不能很好地融入印尼文化,他们是狭隘的美国文化的一部分。”这些美国人所熟悉的印尼人似乎只有家里的佣人。
而到了70年代初,洛洛的新工作使他受到了石油公司的文化的深刻影响。政府要求在印尼的外国公司必须雇用并培训印尼本土的合伙人。有些人认为这种做法太过虚伪:外国公司不得不聘请一个印尼人来作主管,给他高薪,但是却很少或者不让他做任何事情。洛洛的姐夫特里索罗对我说他想不起来洛洛在联合石油公司的工作内容到底是什么。而他的儿子索尼·特里索则罗说,洛洛的工作有可能是“和政府部门搞好关系”。不管怎样,洛洛的工作内容包括和石油公司的主管和他们的老婆结交。他加入了印度尼西亚石油俱乐部,那是一个在雅加达市中心的私人酒吧,专为石油公司内部人员和他们的家人服务,有游泳池、网球场和潜水等各项活动设施。洛洛希望安·邓亨也能参加这些社交活动,如果不能出席,那么洛洛的工作将受到负面的影响。“社会要求她这么做,”伊克兰娜加拉说,“你的丈夫必须带着你出现在社交场合,你还必须穿着"凯恩"和"科巴亚",”这是一种传统服饰,由包裹身体的长袖上衣和一块围在腰间的没有缝线的布穿在下身。“你必须和其他女人们坐在一起,谈谈你的孩子和仆人们之类的话题。”
安·邓亨祈求不要去。“她根本不明白这些习俗,这种过外派人员生活的想法,这种生活和外界世界太过疏远,你甚至需要把自己关在牢房中来保护自己,隐藏自己。”玛雅说。“这对于她来说过于苛刻,而且她已经对此感到厌烦了。”安·邓亨向她的朋友比尔·科勒抱怨说,那些中年美国女子谈论的都是空洞无比的话题。她还告诉科勒说,洛洛“一直都在变得更加美国化”。小时候的奥巴马偶尔会不经意听到父母在卧室里因为安·邓亨拒绝出席石油公司晚餐而争吵。奥巴马在《我父亲的梦想:奥巴马自传》中写道:“在这些宴会上,从德克萨斯和路易斯安那来的美国商人会拍着洛洛的背,炫耀自己巴结了多少人他们才得到了新的海岸油井钻探权,他们的夫人们向我母亲抱怨印尼仆人服务质量太差。我父亲问母亲说,如果他自己去赴宴会怎么样,还提醒她说,这些都是她的同胞。于是我母亲会突然提高声音,几乎喊叫起来:
“他们才不是我的同胞。”
其实安·邓亨和洛洛之间的关系,似乎早在洛洛在石油公司工作之前就开始恶化了。根据奥巴马的描述,在洛洛因为在印尼骚乱时期被召回雅加达而与安·邓亨分开的那一年里,两个人之间发生了一些事情。在夏威夷的时候,洛洛活泼开朗,给安·邓亨讲他童年的故事来哄她开心,向她吐露他回到印尼在大学教书的计划。但是现在,他很少和安·邓亨说话。有的夜里,他睡觉时甚至会在枕头下放一把手枪,有的夜里,安·邓亨听到他“拿着一瓶进口威士忌在房间里游荡,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安·邓亨的孤独一直持续着,奥巴马写道,“寂寞令她无法呼吸”。
安·邓亨曾经从人们不经意说漏嘴的话中把1965年和之后印尼发生的事情联系了起来,试图推测原因。她新结识的印尼朋友告诉过她政府机构、警察和军事勒索中的贪污腐败现象,还有总统随从们的权力之大。洛洛对这些从来闭口不谈。据奥巴马说,最后洛洛的一个侄子向安·邓亨解释了她的丈夫从夏威夷回来之后发生了什么。到达雅加达的时候,他被带走问话,并被告知他已经被强征入伍,要去新几内亚的丛林中呆一年。对有些人来说情况可能更糟,从苏联集团国家回来的留学生直接被关入监狱,或者人间蒸发。奥巴马写道,安·邓亨得出的结论是“强权压倒了洛洛,把他拉回了他以为自己已经逃脱了的境况中,使他意识到权力有多么可怕,而他的生活并不是自己能把握的。”于是洛洛向强权妥协了,“学会了遗忘的智慧,在国家石油公司担任要职,赚了很多钱,就像他的姐夫一样。”
洛洛的行为使得安·邓亨很失望,但是她不愿遵从印尼文化的规则这一点很明显也激怒了他。“和我一样,她根本不知道印尼男人在被家人左右时会变成什么样”林斯克·赫林卡告诉我。她是来自荷兰的人类学家,也是安·邓亨在80年代的密友,也嫁给了一个有一半印尼血统的男人。“印尼男人希望女人在国外的时候大方开朗,但是回到印尼之后,因为有父母,有家庭,你就必须遵从传统习俗,学着做个小女人。你可以把自己打扮得很美,但绝不能太过招摇。我认识安·邓亨的时候,她已经长得很壮实,也不怎么打扮自己,不像印尼女人那样穿衣打扮、佩戴首饰,那完全不是她的作风。洛洛却希望她也这样做。这也是她没有忍耐到底的原因之一。她肯定不会照做,我也能理解为什么洛洛无法接受这一点。”
2009年1月的一个早晨,在安·邓亨曾经工作过的管理学校办公室里,我见到了年近六旬的萨曼。像不少爪哇人一样,他只有单名。他讲一口印尼语,曾和安·邓亨以前的助手菲丽娜·普拉莫诺一起担任翻译,70年代初曾给安·邓亨和洛洛当过家仆。他出生于农民家庭,家里连他一共七个小孩,十几岁的时候他就去雅加达找工作了。在为安·邓亨和洛洛工作时,他主要负责照顾花草、宠物龟、宠物狗、兔子和小鸟,还负责骑自行车或三轮送小奥巴马上学。萨曼说安·邓亨和洛洛付给他不错的薪水,对家里四个佣人也都一视同仁。在他的印象中,洛洛比较严苛,而安·邓亨的心肠很好。
萨曼说,那时候安·邓亨晚上九点才结束授课,有时直到深夜才回家。她似乎不怎么睡觉,经常熬夜打字或者给奥巴马批改作业,然后又在天亮之前起床。萨曼说:“有一次已经很晚了,她和一个学生一起回来,但是那学生没把她送到家门口,于是开车把她送到了住处附近,所托罗对此大为光火。”萨曼后来不经意听到了接下来二人之间的争执:“洛洛说:"我不止一次警告过你,为什么还要这样?"萨曼回忆道。但是洛洛的担心到底是安·邓亨的不忠,还是怕别人说三道四,却无法从萨曼的描述中推断。他说,那次争吵之后,安·邓亨拿着一块毛巾盖在脸上,鼻子流着血,回到了房间里。从这段大约四十年前的回忆中很难推断出到底发生了什么。我采访的其他人都没有提到过两人之间有任何家庭暴力,在大家的口中,洛洛是一个耐心、好脾气的人。
1968或1969年间,一个男教师向安·邓亨问起她的丈夫时,安·邓亨生气地说:“他从来不征求我的意见,从来都是命令我做这做那。”后来反思她的婚姻的时候,安·邓亨用无奈的口气对另一位印尼朋友杨素婉说:“你难道不明白,不要和爪哇人争论,也不要和他们讨论问题吗?因为在爪哇人的概念中,问题根本不存在。时间能解决一切问题。” 安·邓亨曾对一位朋友说,她在身体的宠爱方面对自己的孩子要比她的妈妈对她要亲密得多。她喜欢和孩子们搂搂抱抱,而据玛雅说,她甚至每天会说上百次“我爱你”。她也很喜欢玩制作陶艺,编织装饰品,在家里做铺满了房间的艺术品。“我觉得,当我们和她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获益匪浅,”玛雅对我说。“所以这也弥补了一点她不在的遗憾。”在关于自己孩子的事情上,安·邓亨很容易就动情甚至流泪,即使是偶尔对朋友们说起孩子的时候。她认为幽默好过说教,但对于她重视的事情十分苛刻。理查德·胡克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雅加达和安·邓亨在一起工作,他说她曾经告诉他说她费了很大的力气向自己的儿子灌输公共服务的理念。她希望奥巴马有履行义务的意识,学会回报社会。胡克还说,她希望奥巴马能够怀着她很多年以后才学到的品质去开始自己的人生历程。
奥巴马还记得安·邓亨说:“如果想做为一个完整的人,你就必须有自己的价值观。”有两段评论说,有些时候她不喜欢重复自己的话。唐·约翰逊在90年代初和安·邓亨一起工作,在印尼旅行,有时和她住在一起。唐说:“她曾说过管教奥巴马的事情,比如在奥巴马活该挨揍的时候打他的屁股。”萨曼则说,如果奥巴马没有写完他的祖母从夏威夷寄来的作业,安·邓亨就会“把他叫到他的房间里去,用他爸爸的军用皮带抽他的屁股。”奥巴马也曾通过女发言人表示,他的母亲从未放弃体罚。
萨曼还说,有一天晚上,他和奥巴马在马特拉曼的房子里准备睡觉。他们经常在一起睡有时睡在奥巴马房间的双层床上,有时在餐厅地板上,或者在花园里。那时候奥巴马大概有八九岁,他让萨曼去关灯,但是萨曼没这么做。后来萨曼说,当时奥巴马一拳打在了他的胸上,萨曼没有反应,他打得更重了,萨曼就还手打他。奥巴马开始大声嚎哭,引起了安·邓亨的注意力。萨曼说,安·邓亨没有去安慰他,她似乎意识到了是奥巴马的错,否则萨曼不会打他。
“她不允许我们学得粗鲁,卑鄙,傲慢,”玛雅说。“她教导我们要有点幽默感,要心胸广阔,要努力学习……如果我们说别人的坏话,她就会分析别人的观点,,或者说"如果你是他,你会怎么想?"她有点像强迫我们学会将心比心,不允许我们变得自私狭隘。这种教育从未停止。”
很多人都认为安·邓亨对奥巴马寄予厚望,认为他天赋异禀。她会炫耀奥巴马有多么聪明,多么光荣,多么勇敢。本吉·本宁顿是安·邓亨的夏威夷朋友,她告诉我说:“有时当她说到巴拉克的时候,她说"我的儿子非常聪明,只要是他想做的事都能做成功,当美国总统也不在话下。"我还记得她这番话。”萨玛达尔·马南曾在雅加达和安·邓亨一起教书,她也记得安·邓亨说了相似的话奥巴马可以成为,或者也许梦想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个黑人总统。
萨曼说,一天晚上洛洛问奥巴马:“你长大后想做什么?”
奥巴马回答:“嗯,我想做首相。”
对安·邓亨来说,作为家长,孩子的教育高于一切。但是想让孩子接受优质的教育却很难。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时候,印尼的学校资源严重匮乏,政府严格控制课程大纲,教师资质低下。在印尼的西方人都把孩子送到雅加达国际学校学习,但是这所学校收费很高,而且要就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奥巴马曾就读于两所印尼当地的学校,一所是天主教会学校,另一所是穆斯林创办的。这段经历不可能没有给奥巴马的成长留下影响。爪哇岛人(尤其是爪哇岛中部的)非常重视一个人自我控制的能力。米歇尔·多芙说,连打喷嚏都被爪哇人认为是一种缺乏自我控制力的表现。他和安·邓亨都是80年代在爪哇工作的人类学家,那时候她开始对安·邓亨有了深入了解。“喜怒不形于色,低声细语,安静沉稳,这样你才能被认为是有内涵的人,”他说。强调自控通过取笑别人这种文化变得深入人心,凯·伊克兰娜加拉对我说。她的丈夫(我们只知道他姓伊克兰娜加拉)则说:“人们一直都取笑肤色不同的人。”如果一个孩子被这种取笑所烦扰,他就会被嘲笑得更惨,但是如果他不理会这些待遇,嘲笑就会停止。“我们的大使说,奥巴马就是这样变得冷静的,”他告诉我说,“如果你怒气冲冲反应过激,你就输了,但是如果你一笑而过,你就赢了。”
随着时间推移,安·邓亨对巴拉克未来的发展的想法也有所变化。“她总是鼓励我迅速适应印尼社会,”他在回忆录里写道。“这种做法使得我变得比其他美国儿童要相对要独立,节俭,有礼貌。她还让我学会鄙弃那种海外美国人典型的无知又傲慢的心态。但是现在,像洛洛一样,她也意识到在美国人和印尼人的生活轨迹之间有多么深的鸿沟。她很明白自己想染孩子偏向哪一边,她很确定,我是个美国人,我真正的生活在别处。”
1971年初,安·邓亨告诉奥巴马他要回到夏威夷去,和火奴鲁鲁的祖父母住在一起,去普纳候学校上学,那是一所为人赞誉的学前学校,离邓亨家不远,走路就能到。“她说,她和玛雅很快就回来夏威夷和我会合,最多也就是一年之后,她尽量在圣诞之前就到达,”奥巴马在《我父亲的梦想》中写道。安·邓亨的叔叔查尔斯·佩恩则告诉我说,他怀疑安·邓亨的母亲玛德琳的坚持在这个安排中起到了作用。“玛德琳一向非常关心巴拉克能否接受良好的教育,”他说,“我觉得他认为教育能够带来种族融合所带来的一切问题。”
据奥巴马后来回忆,他离开印尼的时候,安·邓亨的朋友一个飞行员陪着他上了飞机,而“安·邓亨、洛洛和我的妹妹玛雅则留在了门的那一边。”
在奥巴马6岁的时候,安·邓亨把他从美国文化的土壤中连根拔起,移植到了雅加达。现在在奥巴马还不到10岁的时候,她又把他一个人送了回去。不到三年之后她也去了夏威夷,但这次相聚之后,她再次离开了他。
去年七月份,奥巴马在讲话中回忆了这些零碎的事情。“我觉得这次分别对于一个10岁的孩子来说很难承受,即使他表现得没那么在意,”奥巴马说。现在他坐在总统办公室的椅子上,说着他母亲的事,语气中有亲情,也有审慎的距离感。“我上高中的时候,和母亲再一次分开,那个时候我已经长大了,可以很有底气地说:"这是我的选择,我的决定。"但是现在我也为人父母,回想那时候,我会觉得,我当时又知道什么呢,那件事对一个孩子来说并不容易。”
奥巴马在谈论母亲的时候,带着一种喜爱,幽默,和我没有意料到的直率。有时他的语气中还带着一点点温柔的宽容。也许只有一个人被所爱的人磨练了耐心,直到他学会保持安全的距离,才能有这样的感情。或者,这是一个长大了的孩子看到了他的父母并非圣贤。
“她是个很强势的人,有自己的行事方式,”当我问起安·邓亨作为一个母亲有什么不足时,奥巴马这样说。“她非常坚韧,能很快地从挫折中恢复过来,并且坚持不懈,从她完成了博士论文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来。但是除了这些优点以外,她自己并不是一个善于安排的人。你知道,这种安排不当常常造成麻烦。我觉得,如果不是我的祖父母在经济上提供了保障,并且在关键的时候照料我和我的妹妹,我母亲很可能会做出不一样的决定。而且她有的时候容易想当然,觉得"嗯,既然起作用了,那就没什么事。"但事实上,事情不一定总是顺利的,如果没有我祖母所做的一切……如果不是我祖母坚持底线,我估计我们小时候的生活会变得杂乱许多。”
但奥巴马说,他并没有因为母亲的选择而憎恨她。一个成年人的思想的一重要部分就是意识到自己的父母是“有长处,有缺点,有癖好,也有渴望的凡人”。他还说,他并不认为父母只有自己不开心才能把孩子教育好。如果母亲一直情绪低落,他的童年也不会快乐。其实,母亲给他的是父母能给子女的最重要的一件东西“那是一种无条件的爱,它是如此伟大,尽管我们的生活表面上充满了烦扰,但在内心,这种爱一直在支持着我。” (来源:新华国际)
(责任编辑:UN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