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闻背景:
“我不只想写朝鲜的死,还想写它的生。我想告诉读者,朝鲜人不是你刻板印象里的阅兵式上的机器人,而是一个个真实的人,他们也会笑,也会哭,所以当然也会彼此相爱”
芭芭拉·德米克,记者、《洛杉矶时报》驻北京办公室主任,作品有《洛格维纳街:萨拉热窝生死录》《无可羡慕:朝鲜人的普通生活》(台版译为《我们最幸福》)等。2005年,凭着对外事的杰出报道分析,她获得了美国外交学会阿瑟·罗斯奖。 [详细]
黑暗里的爱情
在美国宇航局的夜间卫星照片上,东亚地区闪耀着繁荣的灯光,只有朝鲜半岛北部一片黑暗,暗得就像人烟稀少的青藏高原或西伯利亚。那里并非荒原,而是拥有2300万人口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从1990年代初开始,随着工业以及整个经济的衰退,这个国家和它的夜空一起,慢慢黯淡下来。
长久以来,人们通过各种方式远远地打量着这个国度。它的一切似乎都是政治(或者国际政治)的一部分,供人分析,但人们不会去想,在这样一个国家里,原来也有爱情。
事实上,却是这黑暗赐予人们白天所没有的私密和自由,帮助了爱情的生长。天色暗下来以后,男孩就会躲在女孩家的墙后静静等待——他们的社会阶层不同,如果公开交往会毁掉男孩的前程与女孩的清白。一旦摆脱家人,女孩就会出现。在黑暗里,他们看不见彼此,只是默默地走路,接着他们开始窃窃私语,等他们离开了村庄,谈话就变成了正常的音量。
道路通往一片树林,里面是一个废弃的温泉度假村,长满杂草的池子倒映着天空——从地面往上看,朝鲜有东亚最璀璨的星空,在这样的夜空下,男孩和女孩几乎无话不谈——若干年后,当美国记者芭芭拉·德米克(Barbara Demick)问起女孩,她在朝鲜最快乐的时光是什么时,女孩向她描述了这样一幅场景。
那已是2004年,作为《洛杉矶时报》驻韩国记者,为了解朝鲜的情况,芭芭拉试着联系采访一些“脱北者”。她在首尔以南20英里的水原见到了美兰,女孩已经成了孕妇,丈夫是韩国军队的文职人员。
采访进行一两个小时后,谈话就变成了女人之间的聊天,芭芭拉发现美兰非常愿意讲述她那位前男友的故事,她说他高高瘦瘦,前额留着浓密的刘海,很像韩国一个名叫刘俊相的青春偶像。“我发现她对那段时光很是怀旧,但她生活在韩国人的圈子里,不可能去跟她的韩国丈夫、韩国朋友讲这段往事。”芭芭拉说。
芭芭拉委婉地询问女孩和男孩的关系曾经到了什么地步。“我们花了3年时间才牵手,又花了另外6年才接吻,”美兰回答,“我从来不敢想象除此之外还能做什么。我离开朝鲜的时候都26岁了,但我却不知道怎么才能怀上孩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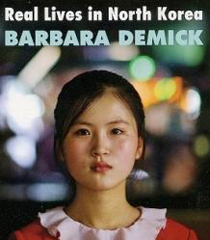
芭芭拉·德米克作品《无可羡慕:朝鲜人的普通生活》
任何事情都不是一成不变的
芭芭拉说,这是她最喜欢的一个关于朝鲜的故事,后来写书时,她决定用美兰和她前男友(在书里,他被称为俊相)的爱情故事来串联全书。“因为我不只想写朝鲜的死,还想写它的生。我想告诉读者,朝鲜人不是你刻板印象里的阅兵式上的机器人,而是一个个真实的人,他们也会笑,也会哭,所以当然也会彼此相爱。”
美兰和俊相都来自清津,朝鲜最北部的一个城市。由于朝鲜政府对外国访问者的严格限制,芭芭拉主要依靠那些离开了朝鲜的“脱北者”了解情况,她采访了六十多位来自清津的脱北者,她相信针对来自同一地区的人员交谈越多,越容易对一些事情进行互相印证。“我得非常小心,要让他们说实话。有时候人们容易夸大其词,有时候又容易非常粗疏。”
此前接受《凤凰周刊》采访时,芭芭拉提到过一个困难:当她询问脱北者在朝鲜的住房条件时,他们的回答大多是“和其他人没什么不同”、“大家都住一样的房子”,因为缺乏比较,所以他们难以讲出他们生活的特点,于是芭芭拉就采取一些特殊的沟通方式,比如要求他们用图画的方式来表现自己的生活,房里都有什么,地板是什么做的,屋顶是什么结构……“通过这种方式,他们讲述了很多令人着迷的朝鲜生活。”
另一些时候,她又不得不警惕某种夸张的描述。“我不觉得这是朝鲜人的问题,和我采访过的其他地区的人相比,朝鲜人更加诚实些。”芭芭拉说,她记得以前读过一个说法,人一天平均要撒7次谎,“有时候他们只是出于礼貌,想要让你高兴,所以告诉你一个夸张的故事。有些日本媒体会为采访付费,所以脱北者有时也愿意把故事讲得更耸动,有些朝鲜人还声称自己参与过核项目等等——对他们而言,如果他们有一个好的故事(从而凸显自己的重要性),能让他们更好地被韩国接受。”
美兰和俊相刚开始时,她还没有高中毕业,而俊相已经考入了平壤一所大学。当他们在黑暗里行走时,俊相给她讲大学的同学、朋友,讲宿舍的情况,讲平壤的见闻,讲双子塔的高丽饭店和深达一百英尺、装饰着大吊灯的地铁站。他甚至去外汇商店给美兰买了一个蝴蝶形的镶着一排排水钻的发夹。因为父亲的出身(朝鲜战争期间被俘虏的韩国兵)不好,美兰对自己的前途并不抱什么信心,她对俊相说:“我觉得我活着毫无意义。”
一回到平壤,俊相就给美兰写了一封信,“任何事情都不是一成不变的,”他鼓励她,“如果你想改变命运,那么你就必须首先要相信自己,通过努力你能梦想成真。”平壤与清津相距大约四百公里,但信件要花上一个月才能到达。相比于黑暗中的面对面,信件是他们更好的一吐衷肠的方式。俊相被爱情俘获,满脑子都是那些经典的爱情场景,虽然他从未看过好莱坞电影。在一封信里他想象着:在美丽的彩霞下,他和美兰跑到一起。

中秋节,一个脱北的家庭来到临津阁的铁丝围墙前祭拜祖先
那些故事,想编都编不出来
芭芭拉这本《无可羡慕:朝鲜人的普通生活》(也有译作“我们最幸福”),讲述了包括俊相和美兰在内6个普通朝鲜人的故事,2010年出版后即登上了畅销书排行榜。有人开玩笑说,因为她的文本太好,故事性太强,让人反而有点怀疑这本书的真实性——其实,几乎所有非虚构作者多少都会面临这样一个角色冲突:做一个“讲故事的人”,还是一个“历史记录者”?
“我想讲述这个爱情故事,不想写得特别政治化、特别沉重,但我也希望人们更多地了解朝鲜社会,”芭芭拉说,“所以我必须平衡,在人性故事与历史中间取得平衡。”
在书中,芭芭拉把大段历史背景压缩进主要人物的生活之中,比如,她希望以美兰父亲的视角来写朝鲜战争,但这显然是困难的——美兰父亲已在朝鲜去世了。于是她选择阅读大量美兰父辈所写的战争回忆录,还去了他在韩国的老家,向与他同辈的老人询问当年的生活与征战情况,“对于描述朝鲜战争来说,这当然是极为有限的视角。也许讲述更多的历史会更好,但我感觉,这会破坏掉故事的节奏感。”
芭芭拉通过美兰父亲进入朝鲜战争,而她进入朝鲜在1990年代发生的粮食短缺,则主要依靠宋女士。
作为一位不折不扣的共产主义信仰者,宋女士曾对那些越来越明显的恶化迹象选择性失明。而整个国家经济的自由落体运动,却正是以停电为表征开始的。在清津,一开始,苗头很小,几乎注意不到。电灯熄灭那么几秒钟,然后是几分钟,几小时,后来,停电变成整夜整夜的,自来水也停了。接下来,口粮配额也开始慢慢消失,宋女士每15天提着两个塑料袋去食品配给中心领吃的,“当他们把袋子还给她的时候,她都不需要看就已失望至极”。
这时国家机器开始宣传“艰难的行军”,平壤的标语牌号召爱国民众“让我们一天只吃两顿饭”,而电视台播放了一部纪录片,一个男人据说因为吃太多米饭,把胃撑爆了。
在饥荒中宋女士失去了她的婆婆、丈夫和儿子——几乎是所有的亲人,但即便如此,在接受芭芭拉采访时,她仍然觉得自己的生活不是最糟的,至少她从未被送进劳动营,从未被人折磨过。
长博,宋女士的丈夫,死前严重浮肿,他对她忆起童年时母亲做的豆腐汤,还有新婚时宋女士为他做的姜葱蒸蟹,他握着妻子的手,眼里闪着泪花:“来,亲爱的,让我们去好一点的馆子,再开一瓶红酒。”丈夫死后,宋女士试图挽救得了肺炎的儿子南玉,但当她发现一支青霉素的价格可以买一公斤玉米后,她选择了玉米。
“死神光临的往往是最老实的人,那些从来不偷、不骗、不坑、遵纪守法,不背叛朋友的人。”芭芭拉写道,“正如意大利作家普。里莫莱维在奥斯维辛死里逃生之后,写到自己与那些幸存者在战后却不再想见面,因为他们所有人都做过见不得人,让人不齿的龌龊事情。当宋女士10年后回首那些时日,当她想起清津那时候死的自己认识的人,她仅仅说了句‘老实,善良的人,告诉他们做什么就做什么的听话的人——他们是第一批死的人’。”
几乎每一位脱北者都有很强的负罪心理,也因此他们很高兴有人愿意倾听他们,“朝鲜人真的很健谈,特别是朝鲜女人,”芭芭拉说,“对这些遭遇苦难的人来说,你就像一个心理学家,是他们好不容易才遇到的倾诉对象。”
宋女士对往事的记忆非常细致,刚刚离开朝鲜暂住中国时,“她每天早晨是被电饭煲的声音叫醒的,她说,这就是我的闹钟,当我听到那标志着饭熟了的‘叮’的一声时,我就下定了决心:再也不回朝鲜了。”芭芭拉说,这本书成功的一个原因,是美兰和宋女士这样的受访者讲述了非常好的故事,“我想编都编不出来。”
宋女士的故事后来单独发表在《纽约客》上,这本杂志有着极其严格的事实核查制度,“他们雇了一名讲韩语的事实核查员,向宋女士核对每一处细节。他们居然问到了她在1990年代早期烧的一顿饭……他们问她,你在书里说,1992年时已经没有食用油供应了,但是你又说,1993年你炒了青蛙吃。宋女士回答说,是拿酱油炒的……”“谁会记得这些!要知道那时已经是2010年!我选的采访对象都是非常值得信赖的。”

韩国首尔,脱北者Kim Han-mi和父亲在家中观看金正日逝世的新闻
朝鲜人不是傻瓜,知道问题出在哪儿
美兰的负罪感来得更加复杂些,她对留在朝鲜的两个姐姐感到愧疚;她对自己的学生感到愧疚——在俊相的鼓励下,她考上了师范大学,毕业后成为一名教师,结果却是眼睁睁看着孩子们一个接一个饿倒;她当然还对俊相感到愧疚,她和妈妈、弟弟的出走决定,是在几个星期之内做出的,她根本没有时间去和俊相道别,而事实上,就算有时间,她也很可能不会告诉他这些。尽管两人几乎无话不谈,彼此却从未吐露过自己对这个国家的真实想法,“这并不是因为她不信任他,”芭芭拉写道,“而是在朝鲜,再怎么谨慎都不为过。”
芭芭拉曾经采访过一位来自朝鲜的工人,他直言不讳地告诉她:“我们朝鲜人不是傻瓜。我们知道问题出在哪儿。但我们不会说出来,我的邻居也知道问题出在哪儿,但他也不会说出来。我们都知道。”
在芭芭拉看来,普通朝鲜人获知真相最重要的途径就是从中国流入的大量DVD,“朝鲜人看韩剧,会更注意韩国人的生活,他们有车有房,房子里有冰箱,冰箱里有这么多好吃的……许多人都告诉我,他们如何从DVD看到了外面的世界。所以,朝鲜是被中国‘腐化’的。”她笑着说。
出发前一夜,美兰把俊相这10年来写给她的信都撕得粉碎,她不想任何人,除了她的弟弟和姐姐,知道他们的美好时光,更不想俊相因为自己的出走遭到连累。她只留下了那个镶着水钻的发卡。
6年后的2004年,当芭芭拉第一次见到美兰时,她戴的还是那个发卡。此后她们经常见面、聊天,2005年的一天,芭芭拉接到美兰的电话:“他在这里!”
原来俊相2004年就到了韩国,为了这次出走,他存了3年的钱,精心考虑了各种可能性,却未曾想到美兰已经结婚。在统一院(韩国为了帮助脱北者融入社会设立的机构)得知这一消息后,他放弃了给美兰打电话的念头,直到一年后在一个聚会被美兰的弟弟撞见。
现在他不得不给美兰打电话了。而美兰在听出俊相的声音后,立刻生气地质问他:“你怎么不早点打电话给我?我们可以帮帮你。”
“他觉得很傻。”芭芭拉写道,“他在韩国几近一年了,这是挣扎的一年,令人绝望的失落、孤独。他可以有一个朋友,特别是一个了解他,而且熟悉他来自何方的老朋友。虽然觉得自己受到伤害,是一个招呼都不打就被抛弃了的男人,但最终却是他道了歉。”
那些刚刚出来的朝鲜人,通常都有着巨大的喜悦,“joie de vivre(生活的乐趣)”,前年10月,芭芭拉在丹东见到一位刚刚抵达中国的朝鲜女孩,“她说,她每咬一口苹果,都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这些人是如此纯真,就好像昨天才刚刚出生。”
宋女士离开朝鲜9年了,一直保持着这种享受生活的状态,“她把自己获得每一样东西都视作一种恩惠,并为此感激万分。”而更多脱北者会经历3个心理阶段,先是非常开心,然后为没能离开的家人感到难过和罪责,再之后会感到愤怒,为他们已经失掉的生活,“你过了那么多年糟糕的日子,你本来早就可以吃上苹果的。”很多人难以融入韩国社会,一些人重新陷入绝望,甚至有人自杀,但也有人慢慢地找回自己。
美兰和俊相约在首尔东部的一个地铁站见面。多年来他就期待着他们的重逢,他甚至还在幻想着那些好莱坞式的场景,男女主角向彼此跑去……结果却是有人在背后喊了他的名字,他转过头去,看到美兰坐在方向盘后,一边摇下车窗一边对他说:“你等了很久吗?”
和在朝鲜时相比,两人的社会关系完全颠倒了,美兰现在属于一个舒适的中产阶级家庭,而俊相不得不从骑车送货这样的底层工作干起——他在朝鲜学到的科技知识已经过时了。
当两人面对面坐下时,都不免有些尴尬。谈起美兰的不辞而别,俊相仍然生气,美兰为自己辩解说,她并不确信自己从此一去不回,她反问他:“如果你计划来韩国,为什么不早点来?”然后她哭了起来。俊相答不上来。一切都太晚了。
此后两人还见过几次面,几乎每次芭芭拉都在场,“好像有我的时候,他们两人不会觉得尴尬。”他们开始互相抱怨,俊相觉得美兰不如以前漂亮了,而美兰则说,现在她很难理解为什么花了这么多年迷恋这个家伙。
如今他们可以很方便地给彼此发短信或者打电话,却很少这样做了。俊相后来通过资格考试,成了一名药剂师,大概在两年前,他认识了一位同样来自朝鲜的女医生,2011年10月,两人结婚了。芭芭拉受邀参加了婚礼。嘉宾里没有美兰。

朝鲜女人的普通生活
栏目策划:王鹏 主持人:沙莎 页面设计:Agui
| Copyright © 2017 Sohu.com Inc. All Rights Reserved.搜狐公司 版权所有 全部新闻 全部博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