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记睡诗”:显“乐天派”本色
林语堂撰《苏东坡传》,开篇原序给苏东坡戴了19顶桂冠,第一顶就说“苏东坡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一语中的,苏东坡当之无愧。读东坡诗词,不难发现:“醉东坡”耽酒,“梦东坡”贪睡,无一不显“乐天派”本色。
东坡现存记睡诗,《春夜》知者较多:“春宵一刻值千金,花有清香月有阴。歌管楼台声细细,秋千院落夜沉沉。”后人常用“春宵一刻值千金”喻指洞房花烛夜,考东坡本意,恐怕还是沉迷“春眠不觉晓”的境界。东坡爱眠,想不入诗也难,诸如“不用撑肠拄腹文字五千卷,但愿一瓯常及睡足日高时”(《试院煎茶》);“要识熙熙不争竞,华胥别是一仙乡”(《次韵张甥棠美昼眠》);“食罢茶瓯未要深,清风一榻抵千金”(《佛日山荣长老方丈五绝》之四),不时可见。
东坡还有一首《醉睡者》:“有道难行不如醉,有口难言不如睡。先生醉卧此石间,万古无人知此意。”被纪昀斥为“俚句”,似可反证纪昀不解睡意。今人喜以猫为师,将“不如睡”视为减压法宝,屡试不爽。
人们平时睡觉,不是卧床就是席地,苏东坡却尝试过《午窗坐睡》:“蒲团蟠两膝,竹几搁双肘。此间道路熟,径到无何有。身心两不见,息息安且久。睡蛇本亦无,何用钩与手。神凝疑夜禅,体适剧卯酒。我生有定数,禄尽空余寿。枯杨不飞花,膏泽回衰朽。谓我此为觉,物至了不受。谓我今方梦,此心初不垢。非梦亦非觉,请问希夷叟。”只要心静,入梦不难,或卧或坐,悉听尊便。
下雨天,留客天,同时更是睡觉天。当年耕耘乡下,逢雨顿生欣喜。有时吃罢午饭,纳头沉沉睡去,待到晚饭被人唤起,匆匆扒拉几口,重返梦乡漫游。家人戏称“连轴转”,说是睡糊涂了。不想此种体验,早被东坡纪录在案:“卯酒困三杯,午餐便一肉。雨声来不断,睡味清且熟。昏昏觉还卧,展转无由足。强起出门行,孤梦犹可续。泥深竹鸡语,村暗鸠妇哭。明朝看此诗,睡语应难读”(《二月二十六日,雨中熟睡。至晚,强起出门。还,作此诗。意思殊昏昏也》)。你看东坡这觉睡得,明明人行街头,感觉如同梦游。欲品此中滋味,至少要有两个前提,一是雨来助兴,二是心无挂碍。香岩评论此诗“极写谪居之无聊,不涉怨怒,斯为诗人之诗”,显然是以己之心,度东坡之腹,皮相之论,诠释过度。
前人评东坡诗,认为多刺时弊,难免招惹是非。不过,像《宝山昼睡》:“七尺顽躯走世尘,十围便腹贮天真。此中空洞浑无物,何止容君数百人。”分明是自我解嘲,不难授人以柄。他人既已借题发挥,东坡不得不出面澄清:“予昔在钱塘,一日,昼寝于宝山僧舍,起,题其壁云:“七尺顽躯走世尘(略)”,其后有数小子亦题名壁上,见者乃谓予诮之也。周伯仁所谓君者,乃王茂弘之流,岂此等辈哉!世子多讳,盖僭者也”(《记宝山题诗》)。这岂不是表白自己不仅没拿野小子当回事,借古讽今,更没把“王茂弘之流”当权派放在眼里?东坡入仕多年,诗人本色不改,福兮?祸兮?
俗谓是福不是祸,果然应在东坡身上。东坡因“乌台诗案”被劾入狱,反对派欲将其置于死地。不料嗜睡爱睡反救了东坡一命。据何薳《春渚纪闻》记载,东坡对友人追忆说:当初案件审毕,一天晚上暮鼓敲过,我正打算睡觉,忽然有人进来,二话不说,往地上扔个小箱子当枕头,倒头便睡。到了四更时分,忽然觉得有人摇我身体向我贺喜。我翻身问他喜从何来,那人只说“好好睡,别发愁”,提起箱子走了。原来皇帝本无杀我之意,特意派个太监到狱里观察,见我睡得鼻息如雷,知道我问心无愧,遂把我贬官黄州。
叶梦得《避暑录话》中说,东坡在黄州,一次“与数客饮江上,夜归,江面际天,风露浩然,有当其意,乃作歌辞,所谓"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馀生"者,与客大歌数过而散。翌日,哗传子瞻夜作此辞,挂冠服江边,拏舟长啸去矣。郡守徐君猷闻之,惊且惧,以为州失罪人,急命驾往谒,则子瞻鼻酐如雷,犹未兴也。然此语卒传至京师,虽裕陵(神宗)亦闻而疑之。”所谓“夜作此辞”,便是东坡名词《临江仙》,全词为:“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馀生。”化解一场风波,功归东坡“鼻酐如雷”。东坡睡功好,从此天下晓。
其实早在贬官之前,东坡就曾流连睡里乾坤,并将此中体会转述给小儿子苏过:“寺官官小未朝参,红日半窗春睡酣。为报邻鸡莫惊觉,更容残梦到江南”(《仆年三十九,在润州道上,过除夜,作此诗。又二十年,在惠州,追录之,以付过二首》之一)。纪昀评价“此首有余致,”大约也是神往于诗中那种“好人好梦”况味。不过,仍是在惠州,东坡只将诗里脉络稍稍延伸一下,没想到惹下麻烦,恰好应验了俗谓是福不是祸下半句——是祸躲不过。
且看东坡这回如何《纵笔》:“白头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曾悸狸《艇斋诗话》透露一段实情:“东坡《海外上梁文口号》:"为报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章子厚见之,遂再贬儋耳。以为安稳,故再迁也。”章子厚就是章惇,此人曾是东坡老朋友,其时正身居相位。老朋友整起老朋友来,下手难免会狠一点。既然东坡在惠州照享“春睡美”,那就贬得再远一点,干脆到儋州去展示“春睡美”,让黎族百姓当评委好了。纪昀为此事深感不平:“此诗无所讥讽,竟亦贾祸。盖失意之人作旷达语,正是极牢骚耳。”岂不知在整人派看来,旷达语与牢骚话从来就是同义词。
东坡初到儋耳,印象最深者,应该是一无所有:“此间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然亦未易悉数,大率皆无耳”(《与程天侔书》)。不过,无室不能无睡,有梦自然有诗:“翛然独觉午窗明,欲觉犹闻醉鼾声”(《独觉》)。为何睡得依旧投入?东坡以自己早年黄州所写《定风波》词结句为本诗作结:“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旧句再用,足可证信念未泯。
纵观东坡一生,仕途跌宕起伏自不必说,连梦境都交织出祸福相倚。敢问拥此奇遇者,旷世可有第二人?(陈长林) (来源:文汇报)

上网从搜狗开始
民生视点
沈阳男子曾令军在这不足20平方米的厕所小家生活了五年,还娶了媳妇,生了大胖儿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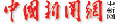 来源:中国新闻网
来源:中国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