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赵文玉(右三)和他的兄弟们。这个家族有17人被查出尘肺病 |
|
|
|
赵红霞带着儿子,穿过结冰的河去给丈夫烧三年纸 |
|
|
|
尚月芳的丈夫在被确诊为尘肺后,为了生活,又去了煤矿打工,结果和儿子一起死在矿上 |
|
|
|
张太山的女儿只有5个月大。他希望能多活两年,看着女儿再长大一些 |
甘肃古浪黑松驿一个人口只有2万的小镇,近三年确诊127名尘肺病人(全古浪县尘肺患者157人),已有11人死去。
这个被死亡笼罩的小镇,正在失去那些乡村劳动力的精华他们怀揣着富裕的梦想去金矿打工,却在几乎没有防护措施的艰辛劳动中,罹患夺命尘肺。
甘肃古浪县尘肺矿工生存报告甘肃古浪黑松驿,一个人口只有2万的小镇,在近3年的时间里,先后确诊尘肺病人127人(全古浪县的尘肺患者是157人),其中已有11人死去。这个被死亡笼罩的小镇,正在失去那些乡村劳动力的精华他们怀揣着富裕的梦想去金矿打工,却在几乎没有防护措施的艰辛劳动中,罹患夺命尘肺。如今,伴随着这些壮年男子艰难的呼吸,他们身后的乡村,也日渐荒芜。
目前,当地政府、网民,以及不愿“坐着等死”的尘肺患者,已展开了救助和自救行动,但无论是未尽劳动保障责任的矿主,还是疏于监管的政府有关部门,尚无人为此承担责任。
傍晚的阳光透过手缝的布帘子,落在杨自发的遗照上。这是一张年轻的脸,如今躲在冰冷的玻璃镜框后,犹自咧开嘴笑着。
在他生命的最后3年,妻子很少见他笑过。他得了尘肺,整天咳,却躲着人。那时,“怪病”的阴影还没有弥漫整个村庄,他心怀恐惧,却不敢对那些和他一起下过矿山的兄弟们说起。
一直到他死去2008年春节前夕,他成为甘肃省古浪县尘肺矿工群体中的第二个死亡者。
几年过去了。如今,他所在的古浪县黑松驿镇庙台村,及其周围村庄,已陆续有上百人被确诊为尘肺。他们构成人数巨大的古浪县尘肺矿工群体。截至2011年1月13日,这个数字是157人。
这些乡村劳动力中的精华、最强壮的男人,在没有任何劳动保护措施的情况下,被“尘肺”一一击中。而他们身后的乡村,也正伴随着他们艰难的呼吸,陷入荒芜。
他自己拔掉了氧气吸管
他整夜坐着不敢躺下,即使跪在炕上,依然喘不上气来。粉尘肆虐的肺部,此时已纤维化,让他无法呼吸。“2008年是我的希望。我要活到那一天,看奥运会!”患病后的杨自发曾给妻子这样说。
可他还是没有等到那个举世瞩目的2008年夏天,在2007年的寒冬,距离北京3000公里的荒芜村庄,他走完了36岁的人生。
家里的牛卖了,粮食卖了,他在矿山打工挣了钱后买的三轮车也卖了,家里再也凑不出钱了!2007年10月,他从医院回家后,病情开始恶化。
他整夜坐着,不敢躺下,即使跪在炕上,依然喘不上气来。粉尘肆虐的肺部,此时已纤维化,让他无法呼吸。“临走的那晚,他用了3罐氧气,一秒钟也不能停。房子里,他吸气的声音大得像打气一样。外面那么冷,他还不停说,把门打开,把窗户打开,吸不上气来……”妻子赵红霞喃喃地说。
晚上9点多,他给妻子说:“我真真把你撇下了,把娃撇下了!”那个夜晚,是赵红霞生命中最寒冷的时刻。窗外飘着大雪,夜里11点,丈夫自己拔掉了氧气吸管,死去了!“我不敢想他受的那些痛苦。”赵红霞的眼泪又打湿了头巾。她拉开衣柜,丈夫当年穿过的外套整整齐齐挂着,洗干净了,看上去体体面面的。“我一件也舍不得烧。”
他俩有一段浪漫的乡村爱情。那年,他21岁,她19岁。她家在30公里外的天祝县。他来村里放电影,一眼就瞅上了她。他自己上门来求亲,“虽说个子不高,但人看起来很机灵,父母就答应了这门亲事”。
他们在县城拍了婚纱照。1997年,他们有了儿子。孩子不到1岁,为了生活,他和村里的年轻人一起相跟着去了1500公里外的矿山。
那是酒泉市肃北县的马鬃山,在茫茫戈壁滩上,距离中蒙边境只有80公里。她只听丈夫说过那里的荒凉、矿井下的辛苦,却没想过,最终,那挖出金子、成全了许多百万富翁的“金山”,会吞噬丈夫的命。
像候鸟一样,丈夫和村里的壮劳力们,总是在正月没过完时就出门。一走就大半年没音讯,山上没有手机信号,一直到秋天收麦时才回来。
时间到了2004年,他回来,说下井时胸闷难受。2005年,病情加重。最终,他在武威市的医院被确诊为尘肺此前,这个病,甚至连县医院的医生都没听说过。
死亡带走了他。曾一心想通过矿山打工改变生活的杨自发,留给妻子和两个孩子的,是连一粒存粮都没有的家,以及6万多元债务。
2011年1月25日,农历腊月廿二,是杨自发的三周年忌日。赵红霞带着儿子,穿过结了冰的萱马河,去给亡夫烧纸。
他死时太年轻,按当地习俗,不能进祖坟。妻子就把他埋在自家田里。那是6亩浇不上水的山地,天旱时,一亩地甚至打不出50斤麦子。
“我们来看你了。你最大的遗憾是活着时没有人关注。现在,这些关注你也享受不到了!”赵红霞跪在坟头,洒下一碗泡开的方便面,又哭了。
“同一个世界
同一个梦想”
孩子们上学的钱在哪?生活怎么办?在检查出尘肺后第二年(2008年),杨自虎去了北京打工。
当杨自发死去时,村里下过井的男人们还没有想到,厄运正降临到他们头上来。
一直到李发忠紧接着死去,人们才被惊醒。李死的时候,和杨自发一样,喘不上气来。在窒息般的痛苦中,脸涨成紫色,两手乱抓,眼睛像要鼓出来一样,十分吓人。
在惊恐中反应过来的人们,突然意识到死者都是去过马鬃山金矿打工的人,此前都有咳嗽、胸闷的症状,而在当地医院,这种奇怪的病早期被普遍诊断为“粟粒性结核”。
42岁的杨自虎,是死去的第4个尘肺病人。他是杨自发的堂兄。
2005年,杨自虎就身体不适。医生告诉他,不能再像以往一样外出打工,所有的重体力活从此都不能再做。
可孩子们上学的钱在哪?生活怎么办?在检查出尘肺后第二年,杨自虎去了北京打工。那时正是奥运会前夕,他在北京地铁的工地上,找了份活。
打工之余,他去了天安门,还拍照留念。有一张照片,是在繁华的北京街头,背景是“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标语,他站在人群中,神情忧郁。
杨自虎是爱照相的。20多岁时,他就借钱买了一个300元的相机,和兄弟们翻山越岭,给乡亲们拍照。村里的年轻人在工地上干完活,休息时,他也喜欢给他们拍照。在那些发黄的照片上,这些农民工们穿着“土气”,却遥望远方,看起来意气风发。
然而,生活击垮了那些曾经的梦想。临去世前,杨自虎在一个破旧的手机上,给自己和妻子银月儿拍了张合影,还做成大头贴。他问妻子:“你知道我是什么意思吗?”那时,妻子心烦,扭过头去,不让他说。如今,42岁的银月儿知道了,那是他留下的祝福,“鼓励我。让我好好活下去。”
她记得大儿子7岁时,他第一次上矿山。一去半年,回来时,已是大年三十的傍晚,门上的对联都贴上了。他笑嘻嘻地从贴身的兜里掏出1000元钱来。
那时候,镇上的干部工资也没这么高呀。1996年前后,他们在县城里的工地上打工,一天8元,在矿山上,一天就能拿到12元!
他们就被这多几块钱的工资吸引着,在下苦力干活时,也一度看到了生活的希望。那1000元,要买年货,买化肥,给孩子交学费……在矿山打工6年,光景好些时,杨自虎给家里买了国产名牌电视机,还买了沙发。
他一直希望孩子们走出连绵的祁连山,再不要重蹈自己的命运。可2010年5月,他终于没等到儿子参加高考,带着那没有实现的“梦想”,他结束了艰难的呼吸。
一个家族的17个尘肺兄弟
在“有钱要大家挣”的想法中,赵氏家族先后有20人投身金矿。2009年在当地政府组织的体检中,其家族的兄弟中17人查出尘肺病。
37岁的赵文玉挠着头,无奈地笑着:“都是我把兄弟们带上山的。”
在已确诊的古浪县尘肺病群体中,黑松驿镇就有127人。而黑松驿的尘肺病人,又集中在庙台村、萱马河村这两个村庄。
赵家在庙台村算大姓。如今,整个家族笼罩在尘肺的阴影中,赵文玉及堂兄弟中有17人被确诊为尘肺。
赵文玉是村里最早去马鬃山打工的人之一。那是1996年,他听堂哥赵文海(如今是三期尘肺)说,矿山上工钱高,就拉了村里的一帮青壮年去了,因为“有钱要大家挣”。
过完正月十五,他们18个人一路搭车向北,到了酒泉市,老板来接他们,敞篷卡车上包个篷布,他们就挤在车厢里,用棉被裹住自己,在戈壁滩上刺骨的寒风中,奔向“希望”之地。
卡车走了一天两夜,他们才来到距肃北县城还有数百公里的马鬃山460金矿。1996年,这一带矿山尚未大规模开发,山上只有一两家个体承包点。
赵文玉和张太山他们,由老板指挥,在生硬的地面上,用羊镐、铁锹,先挖出一个“地窝子”来。地洞上面盖了篷布,地上铺了被褥,这就是他们的住处。
最早是从地面上挖矿洞,粉尘还小些。待矿洞开始开采,就要打眼放炮,人抱着风钻,就在花岗岩上打下去。往往一通干下来,浓密的粉尘就把人裹得严严实实。
为了多挣点钱,赵文玉他们这些最能下苦的壮劳力,干的都是最苦最累的活。在那个时候,在矿山上干几个月,过年回家时,每个人都能揣个上千元,回到贫穷的村庄,引来不少羡慕的眼光。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赵文玉又陆续将自己家族的十多个兄弟带到了马鬃山。他们打工的时间从10年到三四年不等,一直到2009年,在当地政府组织的体检中,赵氏家族的兄弟20人中,17人检查出尘肺病。其中赵文龙已于2008年去世。
除了本姓的家族,他们的姻亲中也有不少的尘肺患者。以赵文祥为例,他的两个妹夫都是尘肺病人,一个是武登奇,已死亡;另一个是周俊山,二期尘肺病人,目前是古浪尘肺矿工自救行动中的关键人物。
在整个黑松驿,尘肺造成的这种家族式“毁灭”处处可见:萱马河村的马召山家,兄弟4人全是尘肺。其中最小的弟弟马江山,是古浪尘肺病人中病情最重的。今年1月26日,一直在家吸氧的他再次病重,住进了县医院。
在庙台村一组,200多人中,就有47个尘肺病人,没得病的壮年男子不超过10个人。
如今,已没有人去埋怨当年是谁把自己带上矿山的,因为,几乎每个上过矿山的人都遭遇了尘肺,而且,有的人已经死了。“死亡不过是迟早的事。”51岁的杨进林说。事实上,死亡一直是隐藏在他们心底的阴影。
“我唯一的心愿是,能多活两年,把孩子拉扯大一些。”马召山忧郁地说。他回头看着躺在炕上呻吟的80岁老母亲,以及炕下8岁的女儿,一脸愁苦。
用了3个月的“一次性”口罩
每次用完洗了,接着戴。就这样洗了几次后,其实已经烂掉了。他舍不得扔,就在口罩里塞了些卫生纸,继续用。
在古浪县的尘肺病人中,诊断为一期的有48人,三期的有43人,其余均为二期。
杨进林是一名三期尘肺病人。三期,意味着病情的严重。在寒冷的冬天,杨进林常常咳嗽,必须随时戴着口罩。
杨进林想不通?自己在矿山打工,前后加起来也就半年时间,检查出来就是尘肺三期。
“在矿上打工的条件太差了,基本上没有啥防护措施。”他说。
杨进林在矿上干的活,是最苦最累的打眼放炮工。一般是3个人一组打炮眼,人抱着风钻,直接在花岗岩上操作,粉尘弥漫,两个人面对面干活,都看不见彼此面目。每当停下时,身上就能抖落几毫米厚的粉尘。
杨进林说,他们下井前没有任何培训,也没有任何防护。有时老板会给他们一个一次性的防尘口罩,但因为一个口罩就要扣5块钱,加上矿山上物资匮乏,口罩也不多,矿工们往往会把这个一次性口罩,象征性地长久用下去。
杨进林领到的一次性口罩,连着用了3个月,直到他第一次下山才扔掉。每次用完洗了,接着戴。就这样洗了几次后,其实已经烂掉了。他舍不得扔,就在口罩里塞了些卫生纸,继续用。
其他的矿工证实,在矿山上,唯一的防护就是这个“一次性口罩”,但因为口罩要扣钱,他们都舍不得用。
杨进林曾听人说,在内蒙古的一些地方,同样是矿山,老板会给矿工们吃些蛋清、猪血,以化解粉尘。他那时就很羡慕。“可在我们这里,什么都没有,每天只吃点面片汤。”
就这样,这些昔日村庄里最强壮、最能吃苦的人,逐渐被粉尘夺去了劳动能力。“你看我这胳膊,一天比一天细了,没一点劲。”马召山伸出自己的胳膊。曾经,他是兄弟4人中最强壮的,可如今,他再也不能支撑起一个家来。
“80后”以及那些活着的人
1981年出生的叶祥17岁就上了矿山,一干就是6年,攒了点钱回家娶媳妇,2009年被确诊为尘肺二期。如今有3个孩子,最小的只有两岁。
杨进林的“挑担”叶祥,是尘肺群体中唯一的“80”后,不久前刚过30岁生日。
叶祥在1998年上的矿山,那时他只有17岁。一直干到2003年,攒了点钱回家娶媳妇。2009年被确诊为尘肺二期。如今有3个孩子,最小的只有两岁。
叶祥有时会羡慕小学班里的少数几个同学。他们上学出来,去了城里,做了“公家人”。
他并不很清楚“80后”这个概念。因为父母去世早,他小学毕业就没有再念书,第一次出门打工就去了马鬃山,结果落下了这个病。
事实上,在叶祥之后,村里那些出生于上世纪80年代的年轻人都不再去金矿打工了。他们有的去了更远的南方,也有的去了内蒙古的煤矿。煤矿上也有粉尘,可“总比在金矿上好”。
赵文祥的侄子赵正文,出生于1985年,如今在北京的服装摊上打工。他的父亲,也是二期尘肺。“到我们这一辈,再也不愿意去矿山上冒死了。”赵正文说。
如今,在被尘肺阴影笼罩的黑松驿,常常有不好的消息传出。2010年5月,水沟村的尘肺患者马永山,去了乌海的煤矿打工。此前,镇上已要求尘肺患者外出打工要备案,但也有一些人为了支撑就要被疾病拖垮的家,再度外出去讨生活。
为了给父亲治病,马永山20岁的儿子先去了乌海煤矿打工,又在煤矿上给父亲找了一个轻松的活儿。马永山就和妻子去了。万没想到,2010年7月,儿子在煤矿上瓦斯中毒,没有救过来。马永山当时气上不来,也死在了矿上。
妻子尚月芳哭着回到了村庄。至今,她不敢看儿子的照片,那是儿子在广州当保安时照的,看上去那么高大帅气。
如今只剩下一个女儿的尚月芳,在有人问起时,只有呜咽。那是压抑的,憋在胸口的无法化解的悲伤。
从2007年至今,在整个黑松驿,已有11个尘肺患者死亡,他们身后留下的是父母妻子和大多未成年的孩子。
在一些失去父亲的家庭,孩子们被母亲交给娘家抚养。赵红霞把8岁的小儿子交给了自己的弟弟;而杨自虎的妻子银月儿,也把今年上高职但无法供养的大儿子,交给了自己的哥哥。
在乡村,失去父亲的孩子被交给外婆家抚养,这是他们的自救方式之一。
2010年8月,失去丈夫的赵红霞、银月儿,还有同样失去丈夫的赵文秀3个人相约出去打工。她们去了新疆摘棉花。平常,她们仨喜欢在一起,因为,彼此“有共同的话题”。
49岁的尘肺患者武登瑞,则在这个冬天花了25000元,买了辆二手的小面包车。他跑的就是从镇上到村里这段路,他的主要顾客,是往返镇上和村里,取药看病的尘肺病人。他的弟弟武登齐已因尘肺死去,留下两个未成年的孩子。
而33岁的张太山,这名年轻的尘肺患者,则常常站在山路上,远远眺望着附近正在建设中的高架桥。如果不是因为尘肺,他原本有可能在工地上找个活儿,以养活他那年迈的父母和5个月大的女儿,但现在,他只能失落地站在那儿。被尘肺击中的身体正在衰落,而他仍怀着生的希望。
本报记者
江雪 文/图
(责任编辑:UN0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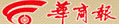 来源:华商网-华商报
来源:华商网-华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