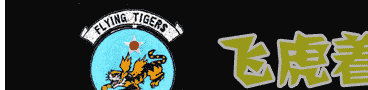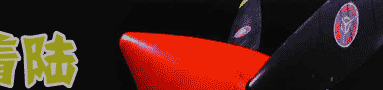| 怎奈归友难逢,各自南北西东,而今俱已耄耋,虽老雄心在,秋晚夕阳红。富贵荣华抛闪,壮志凌云归来。一片丹心献民航,枯荣成往事,何须细述评。
这是年已耄耋,仍被健在的中国飞虎队的老朋友们称为“少壮派”和“红颜才女”的郑兆嘉为纪念两航起义填写的词。今年6月,她给本刊投了一篇关于“飞虎队”和“驼峰航线”的历史事件的回顾文章以及当年飞虎队幸存者重现江湖的文字和照片。根据她提供的线索,《往来》编辑部按图索骥,一一亲临北京、天津、成都、重庆、杭州等地寻访,聆听她的这些拥有半个多世纪友谊的朋友说那些惊心动魄的过往。
如今,年逾8旬的郑兆嘉为了完成健在的老朋友的心愿,还有2002年辞世的丈夫的遗愿,默默地撰写着回忆录,只为,所有的故事,不可以变成黄土。
而郑兆嘉,以她的亲浴战火和经历与任卷任舒的柔美,正是他们中间一颗破解历史,还原真实的胭脂扣。
回望九龙绣成堆
往事闪回,恍如隔世。
回想1949年在香港与先生唐少刚的初婚时节,郑兆嘉仿佛隔着积满蛛网的彩色琉璃,已然感到是另一重天。
那件被雨淋湿后变成超短裙的相思绸旗袍,那个不会说国语,却会煲靓汤的广东籍女佣,那股衬衫、西装、旗袍,甚至手绢和袜子也一定要熨烫平整后留下的清香,那压印着梅兰竹菊精致暗花的信笺……还有,在丈夫难得休息的一天,两人相携去吃西餐,之后去海滨花园听音乐、乘凉,九龙的路灯在绿叶如盖的大榕树上倾泻一地温馨的光亮……
回忆是欢愉的。然而隔着50多年的艰辛路往回看,再好的月色也不免带着凄凉。
不经意间,决定已经来临。
一段时间,有位姓潘的同事常到郑兆嘉的家,与她的丈夫唐少刚在客厅密谈。从小在武汉长大的郑兆嘉听不懂丈夫和同事的广东话。终于有一天,丈夫问妻子想不想回家,郑兆嘉才知道他们正在秘密组织驾机起义。回家,这个消息让思亲心切的郑兆嘉惊喜交集。起身决定,一去不复归,温柔与无畏,怎样融为一体?
刚刚回到祖国的郑兆嘉是幸福的。祖国人民敲锣打鼓,列队欢迎。
曾经在美国学过轰炸机,有编队飞行经验的丈夫的老朋友何其忱同其他两位飞行员一起,负责组织了三个组的编队飞行训练,并于“五一”劳动节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检阅庆典。8月1日,何其忱驾驶DC—3—139号飞机,载着首批14名乘客、邮件、货物从张贵庄机场起飞,与潘国定机长驾驶的“北京”号先后降落在南湖机场。两个机组汇合,参加了武汉的首航庆祝大会,这就是著名的“八一”开航。
光阴的故事,仿佛还在昨天。
落户民航新村
54年前的那个秋日,跟随丈夫到重庆的情景,郑兆嘉又怎会忘记?天那么蓝,草那么绿,空气那么清新,而自己,还是那么年轻。静静的河水淌过脚边,流向远方,然后又折回。跟随丈夫匆匆迁移和匆匆舍弃一份又一份刚刚熟悉起来的工作,郑兆嘉已经习惯了。在看似热闹的变换中,历史和人生正在悄悄改变。
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两航人员及家眷全部调往重庆。参加过“两航”起义的飞虎队员也住在民航新村,大家比邻而居,相互关照。
在重庆大坪郊区突击盖的这片住房,取名“民航新村”。远远望去,红瓦白墙很是漂亮,其实这些住房是用竹片做墙,抹上泥,涂上石灰的简易房。1号喝酒,4号就能闻到酒味;2号钉钉子,尖的一头就透过墙到3号去了。每户一室、一厅、一个洗澡间,一个小间住保姆,四户连成一个单元。
为了支援朝鲜战争,飞行员和家属踊跃捐献现金、银元、首饰。
曾经的飞虎队员何其忱独自捐了一架苏制米格飞机,购买了20根金条的国债。会填词作赋的郑兆嘉担任新村的广播员,每天播放当天报纸上的主要新闻、天气预报和捐款情况。
在重庆民航新村那简陋的房屋中,有时可以听到英姿勃勃的飞行员们用唱机放的唱片,比如,《航空队员进行曲》:“你听,马达悲壮地唱着向前!它载负着青年的航空队员;青年的,航空员!”而白云上空,会碰巧掠过一架飒爽的飞机。
穿旗袍接受改造
1955年1月,郑兆嘉随丈夫唐少刚从北京调到新疆首府——乌鲁木齐,接替因“中苏航空公司”合同期满准备撤离的苏联机组。
她仿佛从繁华的尘世间突然消失了。
大漠黄沙,雪野皑皑,大片的红柳林,随风摇摆的芦苇丛,还有奔驰的骏马和西域的风情见到了她。
她依旧穿着合身得体的旗袍,依旧烫着整齐的发卷,依旧挂着温婉的微笑,虽是流年似水,却芳华仍在,她仿佛是旧社会月份牌上的那些动人女子,仍然坚守着对过去生活的一种执著,忧郁、无奈、平和、坚韧地生活着……任那些或淡雅,或条格,或蔟花的带着主人心情的旗袍,美伦美奂地在“电灯不明,电话不灵,马路不平”的乌鲁木齐机场依次绽放。
环境是极端恶劣的,她的确措手不及。晴天一街土,下雨满地泥。漫长的寒冬,早上要自己砸煤,劈柴生火,晚上清膛倒炉灰。机场外是一望无际的荒滩,除了牛羊肉和土豆白菜,鸡鸭鱼虾和南国的水果只好在梦中相见了。
她和丈夫以及同样从香港归来的两航战友,仿佛是落叶,被风吹到了河里,漂呀漂,很快又被水流冲走,起初的嫩绿一天一天变黄……
那些年,不是梦,是香草飘零。
1964年,丈夫被无故停飞,调往四川广汉飞行学院,改任教员。1968年,丈夫去了陶乐五七干校。郑兆嘉这个“两航人员老婆”“修正主义教师”被“清理”出自己创办的子校,下放到副业队接受“劳动改造”。喂猪、放牛……什么活都做过。甚至在一次给牛卸饲料的时候,从黄河大拖挂上的草堆上摔下来,导致尾椎骨粉碎性骨折,因为不允许住院,落下半生后遗症。
妻子的高跟鞋和丈夫的飞行服,还有那些年轻时的老照片都被强制烧掉。
孩子曾经哭喊:“这里不好玩,妈,我们回去吧!”在塞外陌生的空气中,她也想过马上收拾东西回去,可是,已经来了,就回不去了。
一别经年谁与共
曾经花样的年华,曾经月样的精神,曾经冰雪样的聪明,曾经动人的容颜,曾经……像册中珍藏的厚厚的几十张彩色照片,都是政策改变后,郑兆嘉夫妇以及同他们半个多世纪共同参加过“两航”起义的老朋友们五洲四海重新相聚后的特写。
曾经在政治上、生活上经历了不公正待遇的他们,虽然饱经坎坷,却无一人背叛,即使身在逆境中,精神和生活受到了再大的冤屈和折磨,他们也仍然恪尽职守。因为他们坚信:黑夜过去就是白天!
行文到此,我不由想起1997年去郑兆嘉家做客时的情景。绿色的植物郁郁葱葱,若有若无的音乐在清雅的房间里轻轻流淌。
那时唐少刚老先生仍然健在,虽然头发银白,可是身材高挺,动作儒雅。走进小饭厅后我愣住了。铺着鹅黄色台布的餐桌上,整洁地摆着三套餐具,餐具下压着蓝色格纹餐巾。色彩鲜艳的水果沙拉、烤鸡翅、酱牛肉、青菜、米饭,还有酸奶和一壶沏好的清茶,没有体系,却又自成体系。唐老先生始终微笑着,言语很少。他说,空闲的时候,常常要自己下厨,为夫人做顿西餐犒赏她呢!他同时解答了我的疑惑,两个老人平日的饮食再简单,吃饭的郑重礼仪从未丢过。
该来的都来了,该走的都走了。树丛深处,缓缓走来一对身影,他们相互搀扶着。远处是蓝天、白云、旷野,还有雪山。
|